


伞兵与卖油郎
□徐则臣
(原载《收获》2007年第4期)
1
天很好,万里无云。范小兵背对着我们,酝酿了很久,终于从胳肢窝里拿出了那个东西,对着太阳举在我们头顶。那个东西在刺伤人眼的阳光里,只是一个不规则的黑影子。我们踮起脚尖想换个角度看,范小兵把那个东西又举高了一点,侧一侧手,一道耀眼的红光掠过我们眼前。这下看清了,一个五角星。我们立刻委顿下来,感到了夏日午后的酷热。
“我还以为什么宝贝!”刘田田说。为了表示气愤,她把我口袋里的知了抢过去,掐了一把,带着一路蝉声跑到了树荫底下。
我也很失望。一大早范小兵就放出话,要让我们见识见识,见识什么他不肯说。我们只好等,看着他把那个“见识”夹在胳肢窝里走来走去,我们更着急。他喜欢把他认为的好东西夹在胳肢窝里。我们一直相信他的胳肢窝,那个地方通常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可是现在,他拿出了一个带着汗水的红五星。我一扭头也跑到了树荫底下。
范小兵不着急,矜持地走到槐树下。他又把那个红五星放到我的鼻眼之间,我闻到了一股汗臭味。“猜猜,”他说,“哪来的?”
我懒得猜,“我有十八个,还不止。”
“天上掉下来的,”他把红五星在短裤上仔细地擦了擦,吹口气。“伞兵的,昨天从天上掉下来的。伞兵。”
“伞兵?”
“伞兵。”
我拿过红五星,翻来覆去地看。它跟刚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我说不上来。这样的红五星我有十八个还不止,可是没有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伞兵,这是那个夏天我听到的唯一一个新词。“伞兵是什么兵?”
范小兵没理我,只是仰脸看天。“我要当伞兵。”
范小兵说他看到伞兵的第一眼时,就决定要当伞兵了。昨天下午,他从夏河的姑妈家回来,穿过野地时看到一架飞机经过头顶,慢的几乎要掉下来。他正担心,忽然看到飞机里掉下来一个东西,又掉下来一个东西,一连掉下来五个。往下掉的过程中他看到其实是五个人,他们飞速地往下坠,像五颗巨大的冰雹。然后他们身后弹出一个更巨大的尾巴,像松鼠一样翘到了头顶,紧接着他看到那些尾巴是一顶顶大伞,他们慢下来,如同滑翔的鸟向远方飞去。范小兵想起父亲跟他讲过的故事,他的头脑里一下子就冒出了两个字:伞兵。他跟我们就这么说的,一下子就冒出了两个字,像气泡一样。他当时就两腿发抖,不跟着他们跑不足以平息自己的激动。他边跑边叫,伞兵,伞兵!姑妈让他带回家的一篮子黄瓜都扔了。
他跟着降落伞跑,跌跌撞撞地经过田地和沟坎,摔了三跤。他说他还看见一个伞兵对他挥过手。但是他不得不在乌龙河前停下来,眼看着五把大伞越飘越远。他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也不会回来。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范小兵才悲伤地往回走,两腿软软的。返回的路上发现了那枚红五星,范小兵再一次激动得两腿哆嗦。那枚五角星一半埋在土里,但他坚定地认为,毫无疑问它是某个伞兵的,它从天上掉下来。
范小兵还说,昨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鸟,头顶上戴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我不当兵了,”他举着那颗红五星对我们说。“我要当伞兵。”
2
在知道有伞兵之前,我和范小兵只知道以后要当兵。我们所有男孩子都想当兵,当什么兵没想过,也没法去想,我们不知道兵还要分很多种。我们的理想是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戴军帽,穿军装,头上一颗红五星闪闪发光。我们喜欢所有和解放军有关的东西,为此整天缠着父母,希望能给我们做一身军装,买一根宽大的八一皮带,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但结果相当不好,父母说,哪来的钱做新衣服?酱油都吃不上了。他们都这么说。
我们的愿望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我们一伙人,除了穿了好几年的解放鞋,要么是只有一件上衣,要么是只有一顶军帽,或者是一条八一皮带,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像我,除了一双解放鞋,只有叔叔淘汰给我的一条八一皮带,此外还有十八颗红五星。九颗是我从亲戚家的抽屉里搜出来的,九颗是从别人那里挣来的。我把皮带借给他们勒上两天,代价就是一颗红五星。当然我也送给别人几颗,那是因为我也想借别人的衣服穿两天。所以我说我有十八颗还不止。
范小兵不一样,他家不用打酱油,他家就是做酱油的。海陵人都知道,老范家的酱油那才叫真好。好在哪我不知道,他家有钱我是知道的,大家都知道。老范有钱呢,只进不出,镇上每年还给他钱,逢年过节都要敲锣打鼓地送一大堆好东西给他。老范是退伍的战斗英雄,从前线回家的时候,胸前挂了好几个奖章,一个大巴掌都捂不过来。但是范小兵比我们还惨,老范不仅不给他做军装买军帽,连解放鞋都不给他买。老范说:
“当兵,当兵,当什么兵!好好看书。上不好学就回来卖酱油!”
范小兵说:“我不卖酱油,我要当兵。”
老范抓起酱油端子就要打:“狗日的,还嘴硬!”
范小兵拉着我撒腿就跑。他要把从老范口袋里偷到的两毛钱藏到我家。我们都不懂老范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战斗英雄,在我们海陵,从炮弹里活着回来的就他一个。
“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兵。”范小兵藏在我家的后屋里数钱,加上刚偷到的两毛,他已经是十二块九毛钱的主人了。十二块九毛,多么大的一个钱啊,看得我口水直流。照他说的,只要攒到二十块就可以把别人的军装、皮带、解放鞋都买过来了。也就是说,现在除了没穿裤子,范小兵基本上已经像个军人了。我看着他把十二块九毛钱锁进他的小箱子里,无限神往一个没有穿裤子的范小兵。那箱子是我借给他用的,之前一直盛放我的宝贝,很普通,现在不一样了,在我看来它已经变成了聚宝箱。他把箱子锁好,亲自放到我家的柜子上头。“我要当兵,当伞兵。”
3
伞兵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和刘田田一直都没想明白。范小兵说,记不记得,前年有场电影里放过的,一群解放军绑在伞底下飞。我和刘田田都不记得了,可能碰巧那场电影我们俩都没看。可是没看我们当时干什么去了?露天电影,全村的人都集中在中心路上,我们去哪了?范小兵支支吾吾地说,五月,那晚刮大风,银幕差点吹跑了。刘田田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晚你妈又跑了!说完她立马意识到犯错误了,捂上嘴躲到我身后。
我也想起来了。那是范小兵他妈第三次离开家,也是最后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老范也没再去找过。
那晚上我和母亲搬着板凳去中心路,经过范小兵家,闻到一股浓烈的酱油味。他们家的门大敞着,门口围着一堆人。我挤过去,发现老范坐在屋子里的泥地上,屁股底下全是酱油。一只油桶倒了,流了一地。几个人上去劝他,想把他扶起来,老范就是不起,他像瘫痪了一样低头摸着地上的酱油。范小兵的堂叔从门后抓起一根扁担,问老范:
“追还是不追?你一句话。看我不把她腿给砸断了!”
所有人都看老范。老范摇摇头,突然拍着地大声喊:“出去!都给我出去!”听他的声音一定是哭了。他拍起的酱油溅了别人一身。范小兵的堂叔和一伙人失落地出来了,顺手带上了门。他们在门外议论了一番,范小兵的堂叔说:“我作主了,追!”几个人就跟着他往北走。后面跟了一大趟看热闹的。我和母亲也在里面。那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但因为已经起了风,把声音都刮到别处去了。听不见,我就把电影的事给忘了。
我已经猜到是追范小兵他妈,问母亲,她不愿说,让我不要多嘴。正好碰到刘田田,她也搬着小板凳跟着,我就问她。刘田田说:“除了她还能有谁?看见范小兵了吗?”
“没有,”我说。“可能看电影了。”
范小兵不知道他妈今晚要跑。从第二次逃跑被抓回来,她被锁在家里已经一个半月了。年前她跟辛庄卖豆油的大胡子好上,就把酱油桶扔掉跟人家私奔了。大胡子五十多岁,老婆五年前死了,家里榨豆油卖,赶集的时候都跟范小兵他妈的酱油摊子摆在一起,收市回家时,也顺便帮她把独轮车放到他的小驴车上带回到他们村口。范小兵家没有驴,只有一头黄牛,没有女人赶着牛车去卖酱油的,所以只能推独轮车去。他们常年在一起卖油,一来二去就搞上了,然后范小兵他妈就挺不住了,撂了油桶就想往大胡子家跑。我见过大胡子,他的胡子真好,油汪汪的又黑又长,像电影里的包公,笑起来声音也响亮,像热油下锅。
开头那次私奔,被老范抓回来了,打一顿,关两天就算了,没想到几个月后又跑了,不是从家里跑,而是赶集卖酱油就没回来。三天后,老范的堂弟带着一帮人冲到辛庄,果然从大胡子的床上把范小兵他妈给拎回来了。老范一气就把她锁在屋里,关了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范小兵他妈表现很好,老范就不忍心再锁,趁着村里放电影,就把她放出来看个热闹,也算是补偿。谁知道老范从外面转一圈回来,发现老婆又没了,柜子里的衣服也不见了,还弄倒了一桶酱油。老范围着一地的酱油转了转,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里面。
范小兵他妈那天晚上当然没有追回来,出了村庄就是一大片野地,到哪里去找。以后老范也没再找过,他不想再找了。现在除了儿子和酱油,老范什么都不关心。那晚上我们从野地里回来,继续看电影,但是很显然,我和刘田田已经错过了那个降落伞从天而降的场面。
4
范小兵的脸色先是不好看,接着又好看了。他把手从胳肢窝里抽出来,说:“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伞兵!”
他拿树枝在地上画了一幅画,一个大伞下吊着一个人。很难看,我们还是看懂了。不过我们还是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掉下来,是飘下来。”范小兵都有点急了,他做着飞翔的姿势从一堵断墙上跳下来,摔了个狗啃屎。爬起来又要上墙,我和刘田田制止了。不能让他再摔了。范小兵只好用手当翅膀,一路滑翔,“这样,就这样。”
我们说:“嗯,懂了,懂了。”
范小兵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明白,也就不放过一切机会向我们解释。尤其是天上经过飞机的时候。整个夏天我们都在五斗渠外放牛,我,范小兵和刘田田。野地里没有遮拦,天大地大,总是范小兵最先看见飞机。“快,快!飞机来了!”他把牛扔在一边,跟着飞机就跑。我也跟着跑,希望能交上个好运,和范小兵一样看见伞兵落下来。刘田田跑得太慢,只好留下来看牛吃草。
一次好运都没交到。夏天过了一半,我绝望了。范小兵把没有伞兵落下来当成他的错,更加卖力地向我表演他的伞兵降落过程,看得我越来越糊涂。在范小兵也即将绝望的时候,一架飞机总算撒下了传单。
开始是几张,飘飘扬扬,我们跟着跑,踩坏了不少庄稼。范小兵一边跑一边叫,总算捞回了一点面子。“看,就这样,伞兵,就这样。”但飞机越飞越远,传单突然多起来,一点伞兵的样子都没有了,我只看到大雪花在落。我停下来,范小兵继续跟着跑,大半个钟头才回来,手里一沓纸。他把传单折腾来折腾去,不知怎么就成了一把纸伞的模样,然后拍了一下大腿,说: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刘田田问我:“他知道什么了?”
我说:“不知道。”
第二天放牛,范小兵带了一把雨伞过来,还从别人那里借来了一顶军帽。我们更看不懂了,大热太阳的你带什么帽子和雨伞。
范小兵说:“让你们见识见识。”
为此他建议我们去集中坟里放牛。集中坟是村庄北边坟地的名字,在乌龙河南岸,一大片坟堆,隔三差五长几棵老松和柳。集中坟里草深,而且嫩,但我们很少去。坟地周围的河沟里经常会有死婴被扔在那儿,刘田田害怕。那天我们还是去了,因为范小兵坚持要让我们“见识见识”。
我们把缰绳缠在牛角上,让它们在坟地里随意吃草。范小兵戴上军帽,找了一个高大的坟堆,爬上去撑开伞,腰杆挺直得像一棵树。他要跳了。这姿势让我和刘田田多少有些激动,范小兵要当伞兵了。范小兵啊地叫了一声,声音还没落人就到地上了。刘田田忍不住笑了,我也笑了,我们根本没发现他的伞作用在哪里。范小兵脸都红了,抱怨坟堆太矮,要找个高的。找了半天都是矮的。然后看到了一棵老柳树,高高地伸着一只老胳膊。范小兵说,就它了。他爬到树上,找到合适的位置站好,撑开伞,他的腿激动得直抖,但我们从树底下仰着头看他,还是觉得头顶上站的就像是狼牙山五壮士。范小兵发出了猫头鹰似的叫声,呼啸而下,我们看见他抓着伞像伞兵一样平滑地飞翔了一段距离,落地的时候没站稳,坐到了一个坟头窝里。
范小兵成伞兵了。我羡慕不已,跑上去问他降落的过程中有什么感觉。范小兵喘着粗气说:“有点晕。”
晕过了他又爬起来,继续跳。我想他是找到伞兵的感觉了,尽管我还不知道做伞兵是什么感觉。刘田田却说,他是上瘾了,不就飞么,还能飞过鸟啊?我当然不同意她的说法,鸟是鸟飞,人是人飞。但是,说实话,她的话让我心里稍稍平衡了一点,我也想当伞兵了,可是我不敢跳,有点高。我们都把牛给忘了,范小兵一遍一遍地跳,我和刘田田躺在坟堆上看。
跳到第九次时出事了。范小兵觉得跳得越来越熟练了,想玩点花的,在降落的过程中转上几圈。他说他看到伞兵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就转了好多圈。为了能多转几圈,范小兵改成背对我们跳,在跳下来的一瞬间就开始转第一圈。他做到了,应该说第一圈转得相当不错,错在第二圈,还没转完就落下来了,一头撞到石碑上。我们听到他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我和刘田田跑过去,看到范小兵一手抓着伞,一手捂着嘴哼唧。
刘田田叫着:“哎呀,你嘴出血了!”
范小兵疼得眉眼皱到了一块,对地上吐了一口,全是血。我觉得那血不对头,揪了一根草叶拨了拨,找到半颗牙。我对范小兵说:“把嘴张开。”范小兵艰难地张开嘴,露出破裂的嘴唇和带血的牙齿,两颗大门牙只剩下一颗半。他啃到了石碑。
5
豁嘴唇和断牙没能阻止范小兵当伞兵的热情,倒是老范阻止了几天。他带儿子去医院的路上就决定,不能让这小子再闹下去了。他决定把范小兵看在身边。在学校里他管不着,回了家就他说了算。他逼着范小兵跟他学做酱油,老范一直都说,范家的酱油是祖传的,后继不能无人;出门卖酱油也把范小兵带上,算算帐收收钱,总比让他一天到晚乱跑强。两个星期以后,范小兵又自由了,老范发现整天把儿子拴在裤腰带上,牛没人放了。现在牛正是吃青草的时候,两天闻不到青草味头就耷下来。老范只好狠狠地教训了范小兵一顿,又让他去放牛。
卖酱油范小兵也没闲着,他从钱袋里前前后后摸了四块三毛钱。他把钱藏到我家的时候,脸上俨然是伞兵的表情了。快了,快了,已经穿上大半条裤子了。他跟我说:“我很快就有真正的降落伞了。”
真正的降落伞?
“等两天,会让你见识的。”
我等了两天,看到范小兵从家里偷出了一条床单。
“就这个?”
他郑重地点头。有从口袋里摸出几条绳子,让我和刘田田帮帮忙。
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在放牛的时候帮他做成了降落伞。把床单的四个角分别用一条绳子扎起来,然后四根绳子的另一头再扣在一起。弄完了,范小兵抓着绳头向前跑,有那么一下子床单膨胀起来,但是跑几步就缠在一起在地上拖了。显然是失败了。范小兵不服气,又试了几次,还是没起色。怎么回事?他问我们。我们哪里知道。刘田田头脑一亮,说,不是想让床单膨胀起来么,用树枝撑着。我们就找了两根既细又直的紫穗槐枝条,交叉着和床单四角绑在一起,这样即使没风,床单也是膨胀起来的。又试了一次,降落伞已经能够离开地面了,只是范小兵奔跑的速度和时间都有限,降落伞在空中飘扬了一会儿就坠地了。
我们同时想到了牛。
拴在牛尾巴上,牛比我们都能跑。要范小兵家的黄牛,我们的水牛太笨重。我们把降落伞绑在了黄牛尾巴上,范小兵抽了一鞭子,黄牛闷着头向前跑,降落伞飘起来。就在那个花床单越升越高的时候,噗的掉了下来,黄牛不跑了。它忘了疼。我们兴奋的叫声的另一半,也跟着发不出来了。我想我是见识了降落伞,可惜只壮观了半节地那么远。范小兵还想再抽它一鞭子,我说没用,你总不能跟着它一直抽下去。
第二天范小兵带了一挂小鞭炮。“绑在牛尾巴上,”他说。“我就不信它还能停。”我和刘田田明白了。村东头的小坏孩玩过这个。过年的时候,小坏孩把鞭炮绑在邻居家的牛尾巴上,点着了,那头牛吓得一口气跑了十里路才停下来,差点累得断气。
降落伞和鞭炮绑好了,我和刘田田闪到路边。范小兵点着了火。爆炸声多如芝麻,震得我耳朵里像是飞进了一群小蜜蜂。黄牛发疯似的狂奔起来,降落伞迅速飘起来,鼓鼓胀胀,倾斜着跟在牛身后。降落伞。降落伞。范小兵跟黄牛一样疯狂,粗着脖子狂叫降落伞。我攥紧了拳头,攥得感到了疼。范小兵已经无限接近他的伞兵了。我陡然生出了一阵难受,成为伞兵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那是范小兵的事。刘田田也跟着跳,一边跳一边叫。然后我们看见黄牛突然转身往回跑,那时候鞭炮已经炸完了,但它跑得依然疯狂,闷着头,两只尖角斜向上。降落伞重新飘起来。
“快躲开!”范小兵对着我们喊。
黄牛已经奔着我们冲过来了,四蹄踢踏起的尘土从身后扬起来,又飘又抖的花床单使它看起来像是个巨大的怪物。整条道路都在它蹄子下剧烈地晃动。它扣着头,我看到了它两只血红的大眼盯着我和刘田田。刘田田惊叫起来,整个人僵掉了,我想把她再往路边拉,怎么也拉不动,就在黄牛即将冲到我们的位置时,她突然转身往后跑,只跑了两步,黄牛就冲到了她身后。刘田田的尖叫如同泡沫擦过玻璃,她被牛头高高抬起,她的红衬衫在空中闪耀一下,接着被甩到了地上。黄牛从她身上经过,速度慢下来,降落伞着了地,兜着她拖了很远。我和范小兵追上去的时候,刘田田已经躺在路中间,降落伞的一根绳子断了,把她漏了下来。黄牛继续跑,拖着一条委地的床单。
刘田田一动不动地斜躺着,脸成了一张划破了的白纸。我喊了两声她都没有回应。我和范小兵的脸也白了。刘田田左边的大腿在往外流血,裤子都浸透了,右腿的小腿血肉模糊。我抱起她,不知怎么的眼泪唰的就出来了,接着是哭声。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失去章法地哭过。如果不是范小兵在一边托着,我就是把这辈子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恐怕都抱不动刘田田。
到了医院,我们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很长时间,医生才出来。医生说,小的皮肉伤不算,一只牛角穿过了刘田田的左腿,一只牛蹄踩过她的右腿,还好只是骨肉伤,没有生命危险。刘田田在镇上的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出院的时候成了一个两腿都瘸的女孩。此外,偶尔还会精神恍惚,正吃着饭就咬着筷子发呆。从医院回来,她就再没去过学校。
黄牛是在三天以后找到的,竟然跑到了十五里以外的腰滩。那里有一片浩大的芦苇荡,它在里面吃得肚大腰圆,老范拽着缰绳它还不乐意跟着回来。
6
我们都担心老范会把范小兵打死,他用鞋底一下一下地抽。前几十下范小兵还叫唤,后来干脆不出声了,趴在板凳上撅着屁股,跟睡着了一样。我敢担保,老范一定是用上了当年在战场上杀敌的力气来收拾自己的儿子的,他打得满身大汗,一边打一边吼:
“叫你当兵!叫你当兵!”
打到后来老范也哭了,眼泪跟着汗水一直往下流。打到胳膊再也抬不起来了,打到范小兵的裤子都破了,打碎的布片布条和布丁嵌进了范小兵稀烂的屁股肉里。打到刘田田的爸妈都看不下去了,刘田田她妈哭着说:“不能再打了,再打也跟田田一样了。”
老范停下来,坐到地上,先是看着血红的鞋底,然后抱着被打昏了的范小兵失声痛哭。老范说:“小兵,小兵,你当个什么兵!”好像范小兵已经是个当兵的了。
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老范坚决不同意范小兵当兵,说说都不行。我经常跟范小兵在他家玩,我提起来当兵的事,甚至说“当兵”、“军装”、“八一皮带”这些时,老范都很不高兴。他撂着个脸给我看,我立刻就闭嘴。他当然不会骂我,但范小兵一提他就骂。他说,再兵来兵去的,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他对当兵之类的词和事情,简直敏感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自从老婆跟大胡子跑了以后,每年镇上和村里敲锣打鼓地来慰问军烈属,他都尽量避开。连和军人有关的荣誉都要躲,好像人家不是来慰问他,而是来抓他坐牢的。
范小兵被暴打之后大约半个月,镇上的慰问团又来了。当年老范就是在这样的时节从前线退下来的,这一天成了战斗英雄的纪念日。他们开了一辆大卡车,吹吹打打从中心路拐到老范家的巷子里。卡车后跟了一大群人看热闹,像过节一样。我正在跟范小兵玩,他的屁股还不能靠板凳,必须站着或者趴着,那天他就是趴着,在席子上画自己在跳伞。
我对范小兵说:“又来看你爸了。”
范小兵头都不抬地说:“不在家看什么看。”
时间不长,村长带着两个更像领导的人进来了。背后是喧天的锣鼓,从卡车上一直响到院门口。
“你爸呢?”村长问。
“卖酱油去了。”
“你看看,你看看,太不像话了,”村长很生气。“这个老范,一到关键时候就不在家。”
“没事,”更大的领导说。“这说明我们的战斗英雄觉悟高,自力更生嘛。”
锣鼓继续,更热闹了。几个人抬了一块英雄匾和一纸箱子礼物进了门。老范不在家,仪式只好从简。范小兵从席子上爬起来,代表老范接受英雄匾和礼物箱。领导握着范小兵的手,弄得范小兵浑身痒得难受,但领导一直握着不撒手,对着照相机不停地说话。
最后,领导说:“老范是个好同志,我来两次了,他都不在家,让我很感动。作为一个身有残疾的战斗英雄,他不居功自傲,视荣誉为平常,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我代表镇政府、镇领导,向老范、向我们战斗英雄的儿子,表示崇高的敬意!”
慰问团走了,一些人还留在老范家看热闹。他们想看看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好东西。范小兵打开箱子给他们看。有酒,有高级点心,还有一些苹果和西瓜。我听到一片口水声,谁家能吃上这些好东西啊。看得出来,他们像我一样眼馋。但是范小兵把箱子合上了。范小兵说:“这是给我爸的。”
巷子头的三秃子说:“都走都走,人家是送给残废军人的。你残废了吗也往上靠?”
男人们笑起来,都说:“没残废没残废。”
他们这么一说,我倒愣了,老范胳膊腿一样不少,残哪儿的废?
他们又笑了,三秃子说:“小兵,你妈是不是因为你爸残废才跟大胡子跑了?”
范小兵说:“你爸才残废!你妈才跟大胡子跑了!”
三秃子说:“是啊,我爸残废了,那个东西被打掉了,我妈跟大胡子跑了,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死了。”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范小兵没笑,我也没笑。可是我在想,他爸竟然没有那个东西。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三秃子笑得尤其开心,前仰后合。范小兵一声不吭,从我身边走过去,抓起英雄匾照着三秃子的光头就砸下去。哗啦一声,玻璃碎了一地,三秃子满头满脸都是血,一道道流下来,跟电影里披红头发的鬼有点像。他怪叫着要打范小兵,被拉住了,他们觉得这玩笑开大了,一个个收起了笑脸,匆匆忙忙把三秃子拖出了门。
我一直呆到天黑,到老范回来。老范把独轮车上的酱油桶拎下来,看了看地上的碎玻璃,一句话也没说,找了笤帚扫进了畚箕里。然后打开箱子,抱出最大的一个西瓜让我带回家,我推着手说不带,老范沉着脸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带。一定要带。”
7
范小兵的钱攒够了。他的屁股好了,对降落伞的热情又背着老范高涨起来。那天晚上他把偷来的钱再次放进小箱子里,数完了,说:“二十块零六分。我要成为伞兵了。”然后把钱分成五份摊在我床上。这是帽子,这是褂子,这是裤子,这是鞋子,这是皮带,他说。他已经把所有有军装的人的价格都打听好了,也说定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急不可待地要去找那些有军装的人,现在就买下来。我说已经不早了,谁还不睡觉,明天吧。正好老范来我家找他,范小兵就急急忙忙锁了箱子回家了。
月亮那么好,光照到我脸上,睁开眼就看见掺着蓝幽幽的乳白色。村庄静寂,只有月光移动的声音,是那种琐细的小声音。它让我难受,让我心跳如鼓。我看着从窗户里透过来的一块月光慢慢移动,一直移动到柜子上,我从里到外咯鞛响了一下。小箱子。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转身,转来转去还是看见了那个小箱子。明天范小兵就要成了一个伞兵了,我能想像出来他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全副武装站在高得让人眩晕的地方,背后是他从家里偷出来的另一条床单,当然,现在已经是降落伞了,他向全世界人民喊,同志们,冲啊,纵身跳了下来,降落伞飘飘举举,缓缓而下,他在飞翔的过程中尽情地转圈,转一圈,再转一圈,经过漫长得有一天那么长的时间,范小兵终于落到地上,稳稳地站住,两条腿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地一样,就像本来就长在大地上一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伞兵,但是当个一般的解放军总可以吧。他看上的军装也是我看上的,也许在今天夜里我比他还要喜欢。可是我没有钱。我觉得慰问老范的锣鼓队伍正从我前胸上走过,咚咚咚,咣咣咣,我要喘不过气了。
我爬起来,把手艰难地伸向那个小箱子。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比爸妈都早。母亲问我起那么早干什么?
我说:“去姥姥家。”
“你不是说过两天再去的么?”
“不过了,今天就去。”
母亲很高兴,赶紧给我做早饭。我不喜欢走亲戚,姥姥家都不想去,而姥姥想我去,她说都两年没见过我了,想我都想出病了。我说我去给姥姥看两眼,治治她的病。吃完饭收拾好东西,我走出家门。出了村子我又跑回来,走到范小兵家门口,看到老范正在院子中往一只桶里倒酱油。我跟老范说:
“叔叔,小兵呢?”
“还没起呢。我去叫醒他。”
“别叫了,没事。你跟小兵说一声,我去外婆家了,要什么东西直接去我家拿就行了。”
然后我比刚才更快的速度跑出了村子。一望无边的大野地,我踢着路边的草和露水往前走。右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捏着那一沓纸,捏出了一手心的汗。十三块钱。一件褂子,一条裤子。我知道我穿上那身军衣一定也很好看,解放军就是那个样子。我的左手里攥着一把钥匙,另一把在范小兵那里。左手突然从口袋里跳出来,将钥匙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我看着小钥匙飘飘悠悠下沉的时候才清醒过来,已经晚了。沉下去了。我走了几步再回头,所有水面都长着同一张脸,分不清钥匙落在哪个地方。我站在水边看了看,继续往前走。我是不是跟范小兵说过,就一把钥匙?记不得了。只是十三块钱太多了,我怎么拿了这么多。除了偷瓜,我从来没拿过别人的东西。我一路都在念叨着十三块,直到进了外婆的家门。
我在外婆家住了三天才回来。回到家就听母亲说,小兵这小孩,就是不省心,这才几天啊,又把自己的腿给弄断了。
8
范小兵跳伞的时候把左腿给摔断了。
那天早上吃过早饭,他想等老范出门卖酱油后就到我家拿钱,可是老范吃完了饭一点没有要走的意思。老范说,他要等扎下的小商贩来买完酱油再走。范小兵不知道要等多久,就扯个幌子去了我家,直接抱着钱箱去找那几个要卖衣服给他的人了。整个上午他都在外面转悠,我不知道他打开钱箱是什么表情。或者是一件一件地买,直到最后才发现钱不够了?不知道。反正他只买到了帽子、鞋子和皮带。
我问母亲:“他拿走箱子以后又来过我家没有?”
母亲说:“来我家干什么?”
我松了一口气。可是范小兵他为什么不找我问一问?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想通。那个钱箱子他以后再也没有还给我,为什么不还,我不知道,也不敢去知道。此后我们谁都没提钱箱子的事。当然,那十三块钱我也没有拿去买军装,我把它们夹在一本书里藏在隐秘的地方,一直藏着,中途曾变换过几个地方,直到后来我都记不起来到底藏到了哪里。然后彻底找不到了。
钱丢了也没影响范小兵全副武装地跳伞,他偷了老范退伍时的军装。老范的军装压在衣柜最底下,范小兵拿出来给我看过。那时候他还不敢把它拿出来穿,否则会被老范打死。他挨过打,在他妈第一次跟大胡子私奔那会儿,他只是把军装拿出来在身前比划了一下,被老范看到了,拖过来就打,一连十二个耳光。老范的脸色像黑夜里的判官,声音更可怕,老范说:“狗日的,你再敢把它翻出来,我剥了你的皮喂狗!”
但是这次他抖起胆子把衣服偷出来了。他把帽子、鞋子、皮带和降落伞都藏在屋后的草垛里,开了门回家偷衣服。当时已经是半下午,老范早就出去卖酱油了,是个安全时段。他在打开衣柜之前还是犹豫了好长时间,他得给自己鼓劲,范小兵看到自己伸向柜子的手在哆嗦。柜子打开了,为了不被老范发现,范小兵每一件衣服拿得都很谨慎,按顺序拿出来再放进去,整个过程都很紧张。当他把衣柜合上,一抬头看到老范背对着他站在窗户外,在收绳上晒干的衣服。范小兵慌乱地把军装塞到了床底下,然后站起来说:
“爸。”
老范转过脸找了半天才看见他,“你在家啊?”老范说,继续收衣服。“我还以为你出去了。过来搭把手,把衣服拿进屋。”
范小兵来到院子里,说:“今天回来这么早。”
“卖完了就回来了。”
范小兵趁老范去饮牛的工夫把军装藏到了草垛里。
第二天上午穿上了父亲肥大的军装,袖子和裤腿卷了好几道,八一皮带束住了晃晃荡荡的上衣。他穿军衣戴军帽,英姿飒爽地站在乌龙河的放水闸顶上。那天正好风大,大风吹动的范小兵看上去就是一个英雄。闸底下围了一群像我一样做梦都想当兵的少年。放水闸顶离下面水边的平地至少高十五米,是我们那里能找到的落差最大的地方,没有比那里更适合跳伞了。
后来我听村长的儿子毛小末讲,范小兵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在跳下去的一刻喊什么口号,他甚至连一点声音都没出。他说,范小兵站到闸顶的时候低头对他们说,只有没见过世面的人才会在跳伞的时候大喊大叫,真正的伞兵都是一声不吭地跳的,有什么好喊的呢?伞兵跳伞就像木匠做板凳一样正常,拿起刨子就喊岂不是要累死。范小兵还说,站在高处往下看,感觉真是好极了,他觉得浑身都热了起来,就像煮沸的水一样,他都能听见身体里咕嘟咕嘟冒泡泡的声音,他太想飞了,像老鹰和麻雀那样自在地飞。说完,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跳了下去。
毛小末说,没想到降落伞飘下来的时候那么好看,慢悠悠的,想下来又不想下来,简直都没法相信它是由一条花床单做成的。像一朵花,也像一棵五彩的大蘑菇。范小兵降落的时候也好看,他从容地转着圈,大衣服里灌满了风,如同巨大的花气球下坠着的一个军绿色的小气球。毛小末说,真的,如果不是半路上摔下来,他比伞兵还伞兵。
问题是,半路上范小兵摔下来了。风力那么大,拼命地顶起伞盖,伞盖上范小兵不知道还需要有个排风的洞,交叉绑在四角的两根紫穗槐枝条中的一根突然折断,降落伞的两个角裹到了一起,先是两个角裹在一起,接着另一根枝条也断了,四个角裹到了一起,整个降落伞裹成了一条乱七八糟的装着风的大麻花。离平地五米左右的时候,范小兵像萝卜一样栽下来,毛小末他们都没来得及叫出来,范小兵就摔到了水泥台阶上。那些台阶从河堤上修下来,为了方便人取水的,坚硬而且棱角分明。范小兵结结实实地掉在上面,左边的小腿骨垫到了台阶角上。毛小末他们叫起来,范小兵也叫了起来。
接下来是听我父亲说的,他和老范一起把范小兵送到了镇上的医院。父亲说,在车上老范哭得可伤心了,一手稳住儿子的伤腿,一手捶打自己的脑袋,老范说,都怪他,都怪他,他当时要是不让小兵拿他的军装就不会这样了。他看见了。父亲说,这个老范。
到了医院,还是上次的那个医生,见了老范就说:“你们的骨头怎么老出事,上次是个丫头,这回换了个小子。”
9
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接着说现在。现在,我是一个自由漂游的人。大学毕业后教过几年书,又上了几年学,现在什么也不做,东飘西荡跟着风乱跑。我没当成兵,一天都没当过。高考前军检被刷下来了,平足。范小兵也没当成兵,更不要说伞兵。现在他是一个瘸子,一个孩子的父亲,整天推着独轮车到处卖酱油。范家的酱油做得越来越好了。因为左腿有问题,走路一深一浅,独轮车上左边的油桶从来不能装满,满了就会被颠得溢出来。他的老婆是刘田田,他们很早就结婚了。儿子五岁,名字叫大兵。这名字是范小兵给取的,刚开始遭到所有亲友的反对,当爹的才叫小兵,儿子怎么能叫大兵。范小兵坚持住了,所以现在大兵还叫大兵。这些我都是听我妈说的,我长年不回家,都是在和家里通电话和通信中知道这些事情的。
前段时间我难得回了一趟家,正站在院子里看着墙边的桑树发呆,母亲在门口喊我过去。她说小兵过去了。我伸着脖子朝巷子里看,范小兵已经走到了巷子的尽头,推着独轮车,身体忽高忽低地走,上身挺得直直的。和他一样挺直上身的是跟在车旁的儿子,五岁的大兵,不仅腰杆直,两只手也甩得有力,每一步都把脚尖踢起来,就像一个军人正步走过阅兵台。

徐则臣,著名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长篇小说《王城如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被台湾《镜周刊》评为“2017年度华文十大好书”。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种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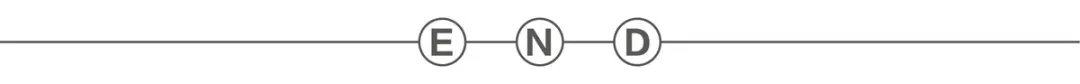
媒体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