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宏新#
文/薛宏新

粪蛋爷腰上那串铜钥匙总在麦黄时节叮当作响。钥匙环是三十八年前用驴牙磨的,齿痕里嵌着麦壳碎屑,遇着东南风便簌簌落金粉。老井台西北角有块青石,经年累月叫钥匙磨出弯月状的凹槽,槽底沉着层麦芒似的铜锈。村里娃娃都说这是粪蛋爷的时光漏斗,要不咋会年年五月石缝里钻出带金线的蜘蛛?
寅时三刻,井绳在辘轳上缠出第九个转经筒的纹路。粪蛋爷往掌心啐口唾沫,掌纹里纵横的沟壑早被井水泡成青灰色。他总说井水在立夏后三日便染了麦魂,要不那蓝釉陶罐里盛的晨露,怎会平白凝出麦穗状的冰晶?昨夜罐沿结的盐霜,原是北斗七星的碎屑——这话是村东头马半仙说的,粪蛋爷听了只把铜烟锅在石臼上磕出三长两短的火星。
老皂角树的咳嗽声比往年早了半柱香。粪蛋爷抄起镰刀敲打陶罐,惊飞麦稍头汲露的蓝蝶。这蝶儿翅膀上的纹路暗合八卦,去年腊月马半仙在蝶翼上瞧见"庚子大旱"的字样,吓得连夜给龙王庙供了三斗麦种。此刻蝶群忽而聚成磨盘大的旋涡,在粪蛋爷草帽顶上盘桓不去,麦芒似的鳞粉簌簌落在钥匙串上,竟把铜锈蚀出蝌蚪文的纹路。
六指蹲在田埂卷烟,豁嘴漏出的青烟蛇一般游进麦田。他那六根指头捻烟纸的功夫是祖传的,烟丝里掺着杏花末子,遇着晨露便膨胀成云絮状。粪蛋爷常说这是勾魂烟,要不然咋会让十年前那个麦客抽了半截,就把自己挂在了歪脖杏树上?如今那杏树枝桠间还缠着半截麻绳,绳结里卡着粒干瘪的杏核,风一吹就呜咽出《信天游》的调子。
日头爬上粪蛋爷的草帽时,麦浪里浮出半截生锈钉耙。这是当年公社化时的老物件,铁齿间缠着的红头绳早褪成灰白色。马半仙说这是钉耙精显形,非要往齿尖抹鸡血。粪蛋爷却拿钉耙勾来歪脖杏树的枝桠,熟透的杏子雨点般砸在麦垛上,迸出的汁水把钉耙锈蚀出梵文似的纹路。六指媳妇在围裙上擦着手嚷:"这可是公社财产!"粪蛋爷头也不抬:"财产?这红头绳还是你婆婆当年的嫁妆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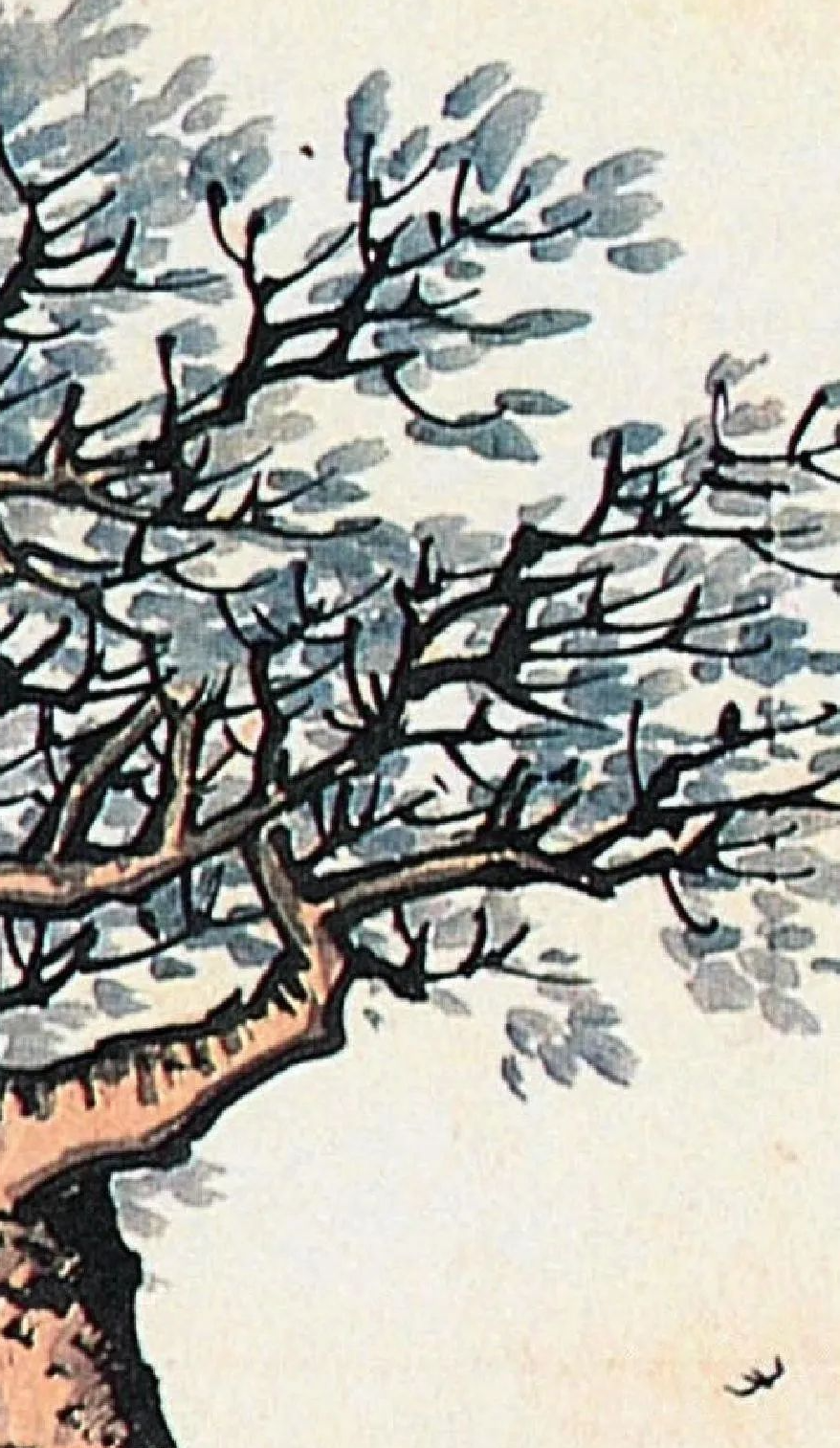
暮色漫过场院时,钥匙串在麦垛上投下符咒般的暗影。粪蛋爷摸出搪瓷缸子,缸底七枚杏核已生出蚯蚓状的根须。这缸子是当年知青留下的,釉面裂痕拼成幅残缺的《丰收图》。六指媳妇送饭时总盯着缸沿的并蒂莲,那花纹与她陪嫁夜壶底款的"莲生贵子"原是一对。去年中秋她偷摸往缸里倒过符水,第二日井台石缝里竟钻出七株麦苗,穗头结的却是杏花。
子夜时分,钥匙串在月光下熔成金水。粪蛋爷说这是麦神在重铸钥匙,要不拖拉机履带缝里怎会嵌着麦粒大小的金疙瘩?六指在麦垛后逮田鼠,忽见鼠须上沾着杏花粉,鼠洞深处隐约传来铜钥匙的叮当声。马半仙掐指算出这是"子鼠盗金",非要在井台烧三天黄裱纸。灰烬飘到歪脖杏树上,竟在树皮烙出《齐民要术》里的嫁接图谱。
五更天露水最重时,粪蛋爷的钥匙串突然绷断。铜钥匙雨点般坠入井底,惊起三只碧眼蟾蜍。井水翻涌间浮上个青布包裹,里头裹着把生绿锈的铜锁——锁眼形状竟与歪脖杏树的疤瘌分毫不差。六指媳妇尖叫着说这是她公公的陪葬物,粪蛋爷却把铜锁往杏树疤瘌上一扣。霎时间麦田里万穗垂首,熟透的杏子噼里啪啦砸开铜锈,每个杏核里都坐着个微缩的麦客,正用麦秆编织金色的钥匙。
晨光染红井台时,拖拉机轰隆声惊散秘术。驾驶座上的杏子不知何时发了芽,嫩枝缠着方向盘长成北斗状。粪蛋爷从排气管摸出把铜钥匙,齿痕间粘着的麦芒突然立起,齐刷刷指向当年知青返城的方向。马半仙的罗盘在此刻疯转,最终停在了老皂角树的年轮中央——那里嵌着半片蓝蝶翅膀,翼梢的蝌蚪文渐渐显形,竟是"戊辰轮回"四个古篆。

薛宏新男,中共党员。曾出版《小河的梦》《婆婆是爹》《可劲乐》等个人文集,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故事会》《故事世界》《民间文学》《今古传奇故事版》《传奇故事》《古今故事报》《当代文学》《河南日报》《新乡日报》《平原晚报》等数百家报刊网络平台,现供职于原阳县城管局,原阳县乐龄书香团成员,原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