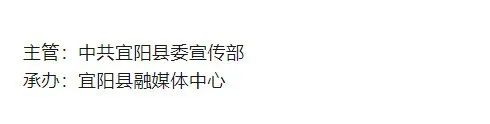第九章
一连月余时日,李贺听的恭维话稠如麻丝,少不得有几分飘飘然。总是稚幼,经不住三句奉承,就愈觉得蜗居昌谷偏僻之地憋屈了自己的才华,便急不可耐地想到东京城里去见识一番。他对父亲求告道:“东京城里文人高士济济,是天下文辞汇流之所,奇景大观目不暇接,诗文相会必能添层才情,长番见识。”晋肃也正为李贺给他带来的骄傲而自我陶醉兴奋不已,见他提出到东京城里去发展求进,哪有不允之理,鼓掌大笑道:“为父已有这层想法,长留我儿于父母翼下,看似爱子,实是误了我儿前程,岂不让人嗤笑为父是老糊涂了?我儿有鸿鹄之志,做父亲的自当倾力相助。东京城是海阔天空之地,我儿也应做志向高远之人,但愿我儿独擅胜场,鹤鸣九皋。”便两下里用工,说服了郑氏。晋肃暂不回任所,也要送到东京城里,把李贺的居所安置妥当再说返程。
次日,一家主婢都忙着收拾到东京城里要用的床帐、被褥及穿戴物什。李贺遵了父命去向好朋友辞行。出了宅院,先行到嵇家,嵇秀才正帮着一个佣工在修缮农具。见李贺过访,羞红着脸抽身把李贺朝堂屋里让,自己去洗手净面。李贺进了堂屋坐下,秀才娘子闻声,出来沏茶侍应,说些客套话。李贺先前还不在意,如今再细看,秀才娘子也是一个好人才,面相娇美,身材俊丰,应酬斯文得体,只是双手皮肤粗糙了些。李贺道:“嫂夫人可好,近几日只顾忙,也没有过来请安少了礼势,还望嫂嫂担待。”
秀才娘子笑吟吟地施了一礼,说道:“哪里有谢字可言,参元贤弟到洛阳城里去住,你也是忙于做诗习文,难有空闲过来相聚,故此总也碰不着面。你兄长常念叨你,得你一半句诗文,能吟到半夜。我对你兄长说,怕是长吉贤弟如今名扬四海,不敢再和咱走动了?你那愚兄却不承认,果不其然,话音这才落地,贤弟就上门来了。”
李贺道:“嫂夫人笑话兄弟了,只因有人来往应酬,无有一星半点闲暇。如若不然,还不踏破你家门槛,还望嫂夫人多多担待小弟的不周。”
正说话间,嵇秀才已收拾利落进来,施了一揖道:“贤弟莅临舍下,愚兄却灰头土脸没了读书人相,辱没斯文,实在是惭愧。”李贺起身还了一揖,两下重又坐了,才道:“哥哥哪里话,农桑之事万户千家谁能少得,辱没斯文又从何说起?前朝陶渊明公可谓大斯文矣,他还吟唱‘田园将芜胡不归’,兄哪来惭愧之有?我倒是钦羡哥哥亦农亦文,洒脱自如,落了个身姿壮硕、精神焕发呢!”嵇秀才淡然一笑,道:“愚兄枉长七尺之躯,别无长处啊!那日李驿丞亲自上门给贤弟送朝廷赠银,吹吹打打煞是热闹,与弟作比,羞得愚兄难出门楣半步。万望贤弟原谅未过府致贺之过。”李贺道:“哥哥所言,小弟愧赧不安,今日登门向贤兄辞行,那些纯粹无聊之事就休提了,免得小弟落下个矫情之名。”
嵇秀才不解道:“居家好好的,怎就言得辞行,莫不是贤弟谋就了什么好前程?”李贺便将欲到洛阳城里暂居一时,入大化之境,以求大进的话说了些。
嵇秀才听了,点头称是道:“贤弟志存高远,愚兄望尘莫及,我昌谷之地的一脉风水全靠贤弟弘扬了。只是一家一家去辞行,过于繁琐,不若相约一聚,一来有个气氛,二来也有了我等给贤弟饯行的礼势,岂不更好?”李贺听了,觉得嵇秀才的话言之有理,便施一揖,道:“还是兄长想得周到,就依兄长之见,选个地处,叫巴童挨家去送请柬。”
嵇秀才道:“地处好选,虞道长处如何?好清静好风光,叙话饮酒如在仙境一般,不知贤弟可否中意?”李贺道:“如此就算议定了。借兄长处写下帖子,叫巴童去各处请了,再安置些酒菜送过去,我与哥哥先到虞道长处奉候便是。”嵇秀才就去取了笔墨纸砚,由李贺写帖。几笔划完,交代给巴童,两人相伴穿竹林幽径朝光武庙而去。
李贺和嵇秀才在虞道长处奉候着,日近天中,人才聚齐。西跨院子陵宫里,有一棵两人合抱的皂角树,树下安放着大石几,酒菜就摆放在石几上。虞道长张罗着众人入席,李一坐了首座,依次大家推让着坐了。道童依次给诸位沏茶,啜饮几盅,都纷纷称道。一壶茶叶冲淡,一坛早已备好的陈年佳酿揭下贴封,掀开盖子,酒香霍然扑鼻,直浸心脾,众人先就醉了精神。
道童一一斟了满杯,虞道长先端起酒来道:“这是贫道藏了十载有余的杜康酒,不遇幸事,轻易舍不得拿出手。刻下为长吉饯行,请先饮此杯,聊壮行色,愿公子前途无量,早求大进。”
李贺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又斟了一杯奉与虞道长,作揖拜谢道:“贺身染重病,全累道长悉心护持,此一杯先敬道长,以谢救命之恩。”虞道长接了饮下,道:“贫道分内之事,何足挂齿。”李贺又斟了一杯奉与李一,道:“世叔对贺教诲提携,可谓用心良苦,小侄对世叔的感激之情皆在此杯中。”朝李一作了一揖。李一道:“昌谷虽好,终非久恋之乡,贤侄有鸿鹄之志,自当展翅高飞。”李贺给在座的逐一敬酒致谢,礼势行完,众人才开始吟诗斗酒。
清风徐徐,满树皂角乱摆,一干人热闹闹地饮酒,不觉间已被风熏得有了几分醉意。虞道长吩咐重又沏了茶来喝,给众人醒酒解酲。自己回了居处,片时转来,肘弯处夹了一件绡衣,展开了原是一件裁缝好了的道帔。说道:“李公子明日将行,想来思去不知该送何物以纪念,忽然记起这件道帔。这也是友人相赠之物,贫道布衣蔬食惯了,从不曾上身,转赠公子最为合适。一来不碍观瞻,二又可避邪驱祟。明朝上路,尽可外罩道帔,贫道敢保公子贵体无恙,百怪不侵。”
李贺接了道帔,上身一试,轻似无物,织丝细密却透明得不掩服色,果然是纱中上品。遂道:“贱体有恙,劳道长百般救护,前恩尚未报答,又受馈赠,贺惭愧之至,请受一礼。”说完躬身作揖。
虞道长赶忙扶住,道:“公子诗名,已至四海,贫道薄赠,受之无愧。还请公子题诗一首,为今日相聚留个念想。”遂吩咐道童铺纸研墨。
待道童们铺排完备,李贺心中已有了诗句,掂起笔来,试试毫锋,挽了袖口,一呵而就,但见诗云:
松溪黑水新龙卵,桂洞生硝旧马牙。
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疋染朝霞。
众人围着看李贺题诗,看完都连声叫好。虞道长开了个头,接下来一个挨着一个亮出已备好的馈赠之物。物什贵贱不等,各有特色。又纷纷依着虞道长的路数讨诗请题。弄得李贺十分难为,又不好失了大家情面,只得凝眉敲额,一一题诗回赠,一伙人直玩到日落西山,晚霞泛红才算作罢。
天昏昏明,一家人不分主仆都已忙碌起来。套车备轿,收拾箱笼,巴童还从李贺房里搬出一沓沓书来,也收拾打包与文房四宝放做一处。不多时有送行的人来,李晋肃陪着说些闲话。一切置备齐整,简单喝了些汤水,就起程上路。李晋肃坐乘官轿,玉儿和巴童要随李贺去,就坐在行李车上。李贺骑在换了绣褥布鞯的距驉上,衣衫簇新,庞眉上挑,一脸好心情。这时天东方刚刚喷红,拜别了送行人,一行车马缓缓而去。
一路上,见衙进衙,见驿停脚。每到一处,都要小停片刻,不为喝茶叙旧,只为李贺以后来住于昌谷洛阳间好有照应。到了洛阳城外,天色已经转暗,城门将要落闸。匆匆忙忙进了城,天已昏黑。宽阔的街面上依旧是人来人往,街两旁的商家店铺掌起了灯,厅堂里明晃晃地生意如常。李贺小时随父来过,但城中的繁闹已记不大准,只能忆起书肆里堆着小山似的书。如今再进洛阳城,心中难免揣着新奇,但亦不敢多看街景。他骑在距驉上,紧紧跟在爹爹的轿后,生怕迷失了。走大街、穿小巷,再走大街、过大桥、再穿小巷,如在梦中迷宫里一般,不辨东西,不知远近,糊糊涂涂地跟了走,直走的人物渐渐稀疏才算到了。在一处宅院前停下,随从上前叫门。不一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一颗头来,问了一声。李晋肃答话,那人赶忙扯开大门,叫着“老爷来京了!”跑过来施礼。李晋肃吩咐拉开门槛,把车轿都安置在院内。巴童从车上跳下来扶李贺下马。李晋肃介绍道:“这是看门人李安,本家子。这是我儿李贺,以后贺儿就长住于此了,你要好生侍候。”李安诺诺连声,给李贺施礼请安。
车轿进了院子,李晋肃指派了住处,便和李贺简单梳洗了一番,父子相随到街上铺子里用饭。留下人们收拾安置妥当了,灶火里柴米具备,做些吃的暂时凑合一餐了事。
次日用过饭后,李晋肃叫人取了送人的礼物,带着李贺出去走动。父子二人说好先到权府拜望。李晋肃告诉李贺,那权德舆如今已不是一般人物,既有先前的缘分,又有权公子相邀,往后就要勤走动,用处大得很呢!按照李贺记下的住址,父子二人一路寻到邻近内城的权府,李晋肃递上写好的拜帖礼单。门子进去回过,放他们进去。有人接住了引至厅堂,从边上耳门进去报过,李贺和父亲坐了候着,有婢子过来上茶。李贺不住来回地看,看不尽朱帘映日,画栋连云,可比三乡驿馆,甚至福昌县衙署要气派多了。厅堂的正中间挂着一幅吴道子的山水,两边围屏对联,俱是名人诗画。正待细看品读一番,忽见才去的家仆进来传点,说公子见客。晋肃示意李贺慌忙离座站起,少刻从屏风后走出权璩权公子来,口中叫道:“是长吉贤弟来了吗?真想死我了!”进厅却是先朝李晋肃行了一礼,道:“不知老世伯一同来访,家父在任上劳碌,已有一年不曾进东京半步,小侄代家父向老世伯致谢,还请担待。”李晋肃还礼,权璩请李晋肃坐。拉了李贺的手与自己一同坐了,道:“是否是老世伯不放长吉一人前来?我还以为贤弟把我忘了。”李贺第一次进这高门大院,有些拘谨,腼腆着脸说道:“小弟早该来的,也想贤兄,只是前段沉疴未愈,家母不放心远行,才耽误至今。”李晋肃笑道:“来了是长住的,以后还望公子照应。贺儿多多过来走动,跟公子多学些个。”权璩笑道:“做父亲的都是这句话,家父也交代我好好跟长吉贤弟学些诗文,老世伯你就别这样交代长吉了,免得我面皮上挂不住。是啥时刻到的京城?安置下了么?没有就先来家住下,我倒是真要跟长吉学些个。”李晋肃答了,又替李贺谦虚自贬一番,自袖中取出一份礼单递给权璩,道:“没啥相赠权大人,薄礼一份,还求公子代权大人哂存。”权璩道:“来就来了,又买什么礼物。”李晋肃道:“一般粗物,难登大堂,送权大人赏人。”权璩道:“倒不好不代父收下了,那可得允我礼尚往来。”吩咐家人去后面取那件豹皮坎儿来。说是天气凉了,回送李晋肃冬天御个寒气,热燥燥的年轻人穿不了。李晋肃一听脸便红了,心想我送一件薄礼,他却厚礼回赠,叫人好不难堪。便道:“公子,本官与相府并无深交,如此回赠,叫老夫怎好再来往?让别人笑我来打秋风不成?”权璩道:“就看世伯礼单,便知您是清官廉吏,陕县任上又能有多少薪俸?一份薄礼再薄,也是世伯心意。我这回赠,切莫往多里想,长吉与我神交已久,就算是我孝敬世伯。”家人抱着一个小包裹进来,到权璩面前打开绿绸包裹皮让其过目,权璩又让李晋肃看了,重又包裹了拿去,让门子送到外面交给从人。
权璩陪着李贺父子说了会儿话,李晋肃便要告辞,说贺儿才来京,人地两生,要陪着多走几家旧好,以后好有个帮衬。权璩说道:“长吉贤弟第一次登门,该留下吃饭的,何必今日就急匆匆地要拜过一遍?”李晋肃说明日他就要回任所去。权璩不便多留,叫李贺写了落脚的地址,说明日便过府拜访,顺便邀一干朋友为李贺接风洗尘。牵着李贺的手一直送到大门外,目送他们父子上马、坐轿而去。
李晋肃又带李贺到铜驼街拜访外戚许国公府第。铜驼街位于内宫之南四会道头,有汉铸铜驼二峰,高丈许,头似羊,颈似马,肉鞍高耸,十分逼真,夹路相对,故此而得名。进了铜驼街,但见街上来往之人着锦衣绣服,气度昂然者居多。也有大家妇女,穿绫披绢的,在人丛里挤挨。街面齐整干净,不时有高大华丽的轩车在金铃叮当中缓缓而过,马蹄叩击着青石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李晋肃的青色小轿在这条街上显得分外的寒酸刺眼。李贺正看得花眼,距驉突然停下来,原来是父亲的轿子停了。他见父亲正从轿窗内探出多半是白须的脸,示意他近前去。他抖了一下缰绳,靠上前去,听父亲说道:“贺儿,这条街会让你看迷的,皇亲国戚多在此地居住,你能看出门道吗?别说是穿青着绿的官员,就是穿紫着绯的朝中大员在此也全能看到,所有投门子的仕途官宦都要走走这条街的。我儿上进,亦不能免。”李贺点头称是。却道:“父亲,后面有人催道呢。”李晋肃这才缩回了头,顿足示意轿夫前行。
终于到了许国公府,却见门外停放着几乘华盖罩顶的大轿,穿着号服的轿夫散漫在轿子周围。李晋肃叫轿夫找一偏僻地界,下了轿子,整衣正冠,牵了李贺的手走上前去。上了几层台阶,至右偏门,刚要递上拜帖,门官却看也不看伸手挡了。李晋肃从袖中取出几两银子递过去,那门子道:“这位爷,咱是相识的,又何必呢?”李晋肃笑道:“给个常例钱,兄弟们也好有口酒喝。”门官道:“那就不客气了。”伸手接了银子,转身进去了。等不多时,见那门官腆着脸出来,干笑着拉了李晋肃的手说:“在下传了爷的帖,无奈今日来的是翰林学士王叔文大人,正与我家老爷商量朝事,不便见客。一上午已挡回去了三个司马,六位侍郎。我看爷暂回去歇着,改日再来如何?”李晋肃无奈,只好赔着笑拉了李贺离去。
出了铜驼街,日已近午。李晋肃还想再找一家拜访,李贺有几分不悦,紧几步赶上轿子,隔着轿帘对李晋肃说道:“父亲,还是回去的好,眼看已到午时,再去拜访不甚合时宜。”李晋肃挑开轿帘看看天,说道:“备好的礼,午后再去总是不如赶在上午的好。”李贺道:“父亲,既是不去拜访也不伤脾胃,孩儿诗名岂是拜了人才传开的?您就容儿自己在这洛阳城里结交一番,也算历练孩儿。”李晋肃听了,挑开轿帘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李贺,说道:“你倒说清楚,是不愿去拜访吗?”李贺道:“豪门大宅的,您尚且不能近身,孩儿一介书生,又无功名,就能随便与他们交往么?孩儿以诗文得名,还要以诗文得第,求人恩宠的事做不来。”李晋肃怔怔地盯了李贺片时,脸上绽出了慈爱、赞赏的笑容,点头不止。叫住轿夫,径直回往南城仁和里。
午后,李晋肃指派李安去购置吃喝用度的一应家什,轿夫和巴童在屋里院内整治。李晋肃带着李贺在方圆左近转了半日,至落黑方回。再进院子,见洒扫拾掇的已十分利亮。李晋肃慨叹道:“这是老父十数年来进京公干的落脚处,如今年迈,再来能有几回?往后就传给你了。”是夜,李晋肃让李贺与自己抵足而卧,父子嗡嗡私语至深夜。第二天李晋肃起轿回程,轿子走了又回,反复数次,做父亲的像是有许多放心不下的事和交代不完的话,日上三竿才算真的出了仁和里而去。
父亲才去,李贺正新鲜地在院子里闲着和下人说话,权璩和杨敬之带着几位相好的公子已经到了门前。常年门前冷落的光景一下子被这几位公子的到来弄得热闹纷纷,李安、巴童忙着拴马,受礼,李贺被权璩牵了手一一介绍。介绍一个,客套一番,几位公子高谈阔论,你说我笑,好一派洒洒脱脱的东京名士风采。李贺初来乍到,又都是新朋友,拘束得很,把一干人朝里让,显不出一点迎客的气度,好半天才把这群锦衣秀士请进院中。李贺吩咐李安快去置酒菜来,又去催促玉儿沏茶倒水。权璩止住李安,说他已订下酒席,即刻便到,只须铺摆桌椅就是。
话音刚落地,就有一辆轿车停在门首。赶车人跑过来问道:“这是李晋肃老爷府第么?”李安应住跑出去看,轿帘撩起,却见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嘁嘁喳喳从车上下来,还带了几个朱漆食盒。李安问道:“是找错了门吧?”女子中有不怯生的说道:“不醒事的奴才,还不快回去问问,是否有个姓权的小爷在?”李安忙进去问,权璩答道:“我便是那姓权的小爷,今儿给长吉接风,图个热闹,从院中叫了几位姐儿陪酒弹唱,叫她们都进来吧。”
几位姐儿一进院子,立时一片欢声笑语。引进房里,相携入座,酒菜摆了上来,一会儿就成了觥筹交错,热气腾腾的场面。李贺未曾经过这种场面,见识又少,一个好端端的主家无言无语地坐着,羞答答地像个小娘子。不多时,光敬酒就吃了十数盅,吃得红头涨脸,有了几分醉相。权璩道:“前几日听姐儿们唱《天上谣》,制词度曲好,姐儿唱得也好,余音至今不绝于耳,能否歌来再听听,助各位下酒。”几位姐儿听了,哪有不依,便离席操琴持管,歌舞起来,歌曰: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秦妃卷罗八方晓,窗前食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姐儿们唱着,在座诸位纷纷击节附和,歌毕,赞叹叫好声一片。
权璩见姐儿们一曲歌罢,又点一曲《神弦曲》,歌曰:
西山日没东山昏,旋风吹马马踏云。画弦素管声浅繁,花裙綷纟卒纟蔡步秋尘。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帖尾,雨工骑入秋潭水。百年老鸮成木魅,啸声碧火巢中起。
歌罢,权璩问打头的姐儿,道:“姐儿们歌弦悠美,实是高手妙制,但可知这作词之人为何方神圣?”打头的姐儿道:“妾所弦歌之词,皆是东西二京风靡之歌词。是宗人李贺所制。”权璩又道:“是姐儿找李贺求的词吗?”打头的姐儿道:“贱妾哪识得如此人物,是爷儿们爱听他制的词,便到教坊里学了几曲应个景儿。”权璩笑道:“既如此,几个姐儿就各罚一杯酒吧!李贺在此,你们却不识他真容,还唱他的词,不怕他找你们要润笔之资?”几个姐儿听了,放下手中物件,笑嘻嘻地围过来,自斟自饮,每家一杯。搬着众位公子的脸问哪个是李贺相公?权璩把李贺拉起来,道:“长吉贤弟,叫几个姐儿陪你吃几盅花酒,也算认识一回。”众人纷纷起哄,几个姐儿扯扯拽拽把李贺围了个严实,执壶斟酒争相要与他喝个交杯。
李贺没见过这种阵势,窘迫难耐,又无从脱身,只有胡乱地应付。一干人看着他的狼狈相窃笑。在座一位稍嫌年长姓谢名魁的秀才道:“长吉贤弟尚不谙熟风月之戏,尔等怎能一味胡闹,略施些温存才可入局。”经谢魁一说,姐儿们才收了疯性儿,一个个娇滴滴、甜蜜蜜地绕着李贺使手段。打头的姐儿竟还备着名刺,要留给李贺,求李贺过馆一顾。李贺看了名刺,见上写“琅轩馆”,平康里入北门东回南曲,水荭。收进袖中,连声应承。也不知是喝得还是羞得,一时间面皮通红,言语也不顺畅。正好玉儿过来奉茶,见了心疼,劝说道:“小爷,莫敢多饮了。”大伙儿正在兴头上,见婢子劝阻李贺,立马都止了声。水荭手里端着一杯酒,正挽着李贺要饮,弄得好没脸面,便憋屈着放了酒杯,问道:“这位姐姐是……”李贺怕生误会,忙道:“这是家养的婢子玉儿。”水荭扑闪着大眼看着玉儿,环顾左右道:“我说呢,谁会这样萦记李公子?虽无夫妻之分,却有夫妻之实,爱惜心疼李公子也是无可挑剔,姐儿我就把这杯酒自饮了吧!”说完一仰而尽。大伙听水荭说罢,笑语喧阗。玉儿哪经得住水荭这般挖苦,转身躲出去了。权璩道:“玉儿哪是心疼李公子吃酒,是怨你们一班姐儿劝酒惹她吃醋了。今儿不该让长吉独占花魁,免得后院起火。还是大家一起作局吃酒罢。”李贺已真是饮得到了量,见权璩圆场,忙向姐儿们施礼告饶,才算得以喘息。
一干人行令饮酒作乐,至入夜方罢。水荭已饮得醉了,非要闹着与李贺同宿,被众人哄着才去了。这边送走一起儿,那边却又有了事。原来玉儿受了水荭奚落,心中窝着气,又不便找了去闹,躲在屋里暗处哭。等人都去了,才使出小性儿。李贺饮多了酒,着急要睡,玉儿不但不侍候,还不住地数说。说想着小爷是到这洛阳城里长见识,想不到招了这样一干子人,男男女女的胡混在一起,净做些不入眼的勾当。自己没脸没皮了,还要揭挑别人!她要真是有头有份的也就算了,偏是个人尽可夫的花妓也敢来糟践别人,小爷偏就能忍了。李贺好言好语地哄她几句,不想倒招惹起她的犟脾气,一味地坐大,嚷着要李贺明日就送她回昌谷去。巴童进屋来劝亦劝不下,惹李贺恼了,扯着嗓子吼她,还发誓赌咒要卖了她,才算怕了。抹着泪把李贺服侍睡下,自己又躲去外间嘤嘤地哭。弄得李贺睡不安稳,不得不重又拿软话来哄,一同熄灯睡下,百般抚慰才算安生。
▼
往期精彩回顾
▼
付涛到上观乡调研指导工作
陈宝国到锦屏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选民主题活动
王少杰到柳泉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联系选民主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