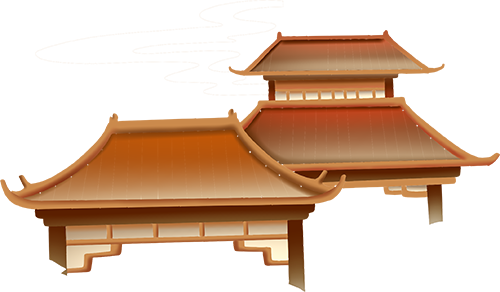
模仿、重建、融合:
论余华《河边的错误》的电影改编
闫煊煊
本文提要
《河边的错误》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钟山》1988年第1期,于2023年被导演魏书钧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电影中有对小说主题,即不确定性、错误以及河流的模仿;有以小说为基准,抓住错误这一侧重点对小说框架进行的重建;也有小说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分离。由此实现了电影对于小说文本的创造性转化。
一、模仿:文本与影像的“同工”
《河边的错误》这部电影所构建的世界观,所渲染的氛围都抓住了小说中所体现的不确定性、“错误”以及“河流”这些意象,与小说都采用了开放式结局,为观众与读者创造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一)不确定性
后现代哲学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不确定性”。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尼采也曾指出:“与我们相关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即不是事实,而是建筑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世界是‘流动’的,是生成的,是不断推演的,是从来不曾达到真理的假象,因为——没有什么‘真理’”,“事实是没有的,万物皆流,都是不可把握的,退缩性的。”不确定性这一特征在《河边的错误》小说与电影中均有体现,并且反复出现,或明示,或暗示。大到主题小到人物的名字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首先是主题的不确定性。小说与电影都以幺四婆婆遇害为开篇,随之又让观众和读者以刑警队长马哲对案情的梳理为主线往下推进。在观众和读者以推理小说的套路观看时,思绪反倒越来越模糊,阻挡在真相前的迷雾反而愈加浓厚,直到最后读者和观众才明白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推理悬疑小说。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是余华对先锋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先锋小说的主旨不在于摹仿,而是自我表现,展示世界真相,以及探讨生存哲学,它是一种从自我存在出发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小说。因此,在这部小说或电影中,我们不应抱着看悬疑小说或电影的态度去寻求一个确定的凶手,而是要将其作为一种选择,继而去探寻这部小说或电影更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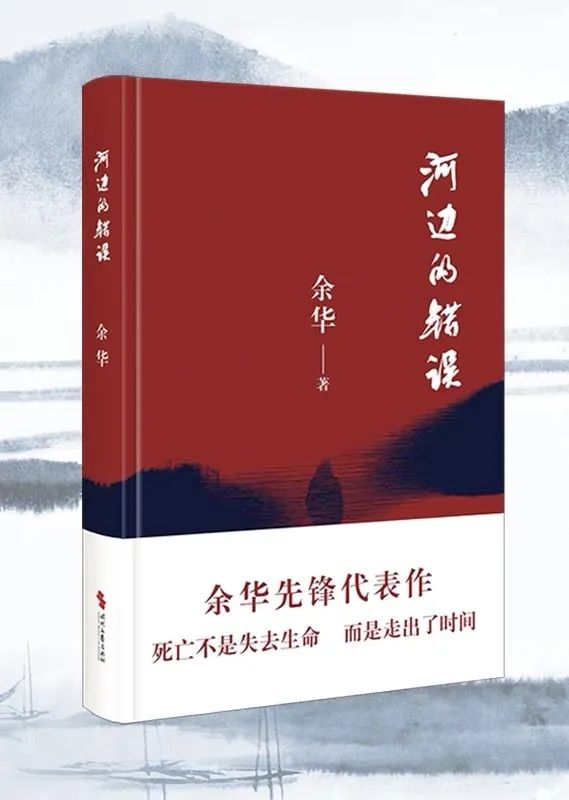
《河边的错误》
余华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23
其次是人物的不确定性。这些人物并非“有血有肉”的,不会具象到某一个人,他们只是作为符号代表着某一类人。如第一幕出现的受害人幺四婆婆,无论是引出主旨还是推进剧情,都有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在这里,她只有个代号,不仅指名字,连幺四婆婆的为人也都只能从邻居的口中得到部分了解。另外一个受害者——小男孩,在这里代表了希望获得大人的尊重与认可的一类孩童。他有着异于同龄孩子的冷静和果敢,与“警察”这一角色处于同等地位交谈使他感到骄傲,但是直到离世,小说与电影中都没有提到小男孩的名字。马哲的妻子也代表着千千万作为公职人员的丈夫因繁忙工作而无法对家人有着合理关爱,以至于孤独无依的妻子形象。
再次是凶手的不确定性。在幺四婆婆遇害之后,马哲根据线索依次找到嫌疑人并进行审问。依据作案工具柴刀与丢失的财产判定凶手的目的是得到钱,而在马哲搜查“疯子”房间找到柴刀却没找到钱时,马哲的线索断了。他找不到“疯子”的杀人动机,家里出现的作案工具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疯子”的独特性,他无法为家里出现的作案工具辩解,他也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凶手的踪迹再次隐掉了。
最后是“疯子”的不确定性。案件一直未侦破,线索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相关证人或目击者一个又一个地逝去,马哲的心理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变得扭曲起来。小说中,马哲的妻子和同事为了使马哲逃脱法律的制裁,就让精神医生反复逼问,终于马哲语言混乱,“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啊。’”马哲也成功被送去精神病院。电影中,马哲的精神状态更为扑朔迷离,观众也跟随马哲的内心,在现实和幻想中反复横跳,分不清真假虚实。他心心念念的三等功没一个人记得,他自首承认是自己开枪杀了“疯子”,然而枪里的子弹却丝毫未动。家庭和事业的压力让马哲喘不过气,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又有间接因自己而受害的证人,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将马哲也逼成了一个“疯子”。
(二)错误
“错误”一词在词典中的释义是不正确,与客观实际不符,或者指不正确的认识、行为、动作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错误也不是绝对的。虽然小说与影视都以《河边的错误》为题,但“错误”一词在小说和电影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案件中每个死去的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错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两面性”,一面是为了融入大众,另一面是真实的自己。幺四婆婆一面是一位孤寡的老人,不愿和街坊邻居往来,另一面则是有着受虐心理、将“疯子”视为自己死去的丈夫的人。另一个人物许亮在小说与电影中是两种不同的形象,但也都有其两面性。在小说中,许亮一面孤僻一面开朗;在电影中,许亮是厂里的理发师,私下里却有着“异装癖”。还有王宏,一面是德高望重的老师,一面却与钱玲维系着地下恋情。小男孩在父母眼中是无知胆小的孩子,而实际上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冷静与勇敢。
除了幺四婆婆的受虐倾向、许亮的“异装癖”、王宏与钱玲的地下恋情、小男孩超出其年龄的大胆等“错误”之外,马哲的错误贯穿了整个故事线。他沉溺于自己的“神探”角色,电影中为了查案他害了与案件无关的许亮,因为不相信凶手是“疯子”于是将其释放,间接又害了小男孩和王宏。
(三)河流
“他知道,获悉这条河的秘密,就能获悉许多别的秘密,所有秘密。今天,他从河水的秘密中获悉一个撼动灵魂的秘密。他看见河水不懈奔流,却总在此处。永远是这条河,却时刻更新!哦,这谁能领悟,谁又能懂得!他不能。他只感到河水激起他遥远的记忆,激起神的声音。”悉达多在倾听河流中参悟到了人生的意义,河流如同一位智者,为人指点迷津。在《河边的错误》中,河流也扮演着全知的角色,它不仅仅是连接县城与小镇的唯一通行方式,它还“亲自”见证了多起凶杀案的发生。正如电影的英文名Only the River Flows,没人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这一切的见证者只有河流,也只有河流知道真相。
二、重建:文本与影像的“异曲”
电影以小说为基础,将小说中架空的人物及历史背景进行了填充,以“错误”一词为切入点,分别赋予了四名典型人物与故事背景所不符的性格或事件,这使得他们的存在成为“错误”。电影中对人物数量及人物故事的增删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也为这个荒诞的故事注入了真实的重量,补充出了较为完整的故事链,丰富了影片中时代和社会背景。
(一)故事逻辑的重新架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争爆发、科技飞速发展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科学与理性成为主流思想。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加缪在《卡利古拉》中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电影《河边的错误》开篇引用的是卡利古拉对其仆人西皮翁说的话,“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卡利古拉因为爱人的离世悟出了人生的真理,他决定要追求超越“神”的东西,想要化不可能为可能,他认为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而恰巧他作为帝王,有手段可以让他的子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他的一系列决定和政策的实施都为了证明在自己的疆域内,他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制订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电影在开篇对《卡利古拉》的引用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生命个体与荒谬的斗争,从而引发了观众对真理,对生命哲学的思考。

《河边的错误》电影海报
《河边的错误》小说中对真假、虚实以及生死等哲学议题都进行了讨论,而电影则以“错误”为出发点,对整个故事逻辑进行了重新架构。这一错误指涉的是个体与荒谬的斗争,电影将片中人物分为五个受害者,他们的行为因为与当时的道德观念相悖,从而被定义为“错误”。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真理的表象也是流动的,并非一成不变。何为对何为错,关于真理的标准,每个时代都不尽相同,他们作为浪潮的牺牲品,作为渺小的个体去与年代的庞大的荒谬作斗争,这本身也是一种荒谬。电影将受害者痛苦的生存内容与荒谬的受害形式巧妙结合,每一个犯“错误”的人都是时空的缩影,从而引发观众对真理对命运的思考。
(二)人物形象与叙事的增删
电影为了更有逻辑性,以小说为基准,通过对小说中已有人物进行细致刻画,或增加辅助性人物或事件来充实角色使电影的逻辑完满。因此部分人物形象的构建相对于小说来讲更加饱满立体,整部电影的逻辑也更为清晰明了。实际上,电影也为“荒诞”的小说套上了“逻辑”的外衣。
电影新增了钱玲与王宏的故事。首先,在小说与电影中,王宏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形象。小说里,王宏性格孤僻,少与人交往,面对警察时总是气势汹汹,王宏的妻子在王宏去世后变得精神恍惚、麻木。在电影中,王宏妻子的角色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钱玲这一角色,他们之间的感情则是属于他们的“错误”。他们因喜欢诗歌而产生感情,在电影的隐秘刻画中,他们的感情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因诗歌相爱,认为彼此是对方的乌托邦,是对方在那个荒谬世界里的唯一情感寄托。在钱玲被刑警马哲顺着线索找到后,王宏懦弱且胆小怕事的性格立刻彰显,他为了不让自己受到牵连,主动找到马哲说明情况并表示自己与钱玲的关系无法公开,希望警方不再对他追问。
电影丰富了马哲妻子与他之间的情感。小说中对于马哲妻子的描写较少,只以简单几句带过:“他的妻子也惊醒过来,睁着眼睛看丈夫穿好衣服,然后又听到丈夫出去时关门的声音。她那么呆呆地躺了一会后,才熄了电灯。”寥寥几句关于妻子动作和神态的刻画,点明了他们夫妻二人之间聚少离多的无奈。电影对于妻子的刻画更加饱满,除了别易会难,马哲与妻子之间关于孩子的去留问题也是争吵不休,这一分歧是他们后续一系列矛盾的激化点与导火索,也为马哲最后走向精神分裂作了铺垫。在马哲与妻子在卧室谈话的镜头中,马哲被镜子分割成了三份,这一镜头也是暗示了马哲的最终结局。
电影删减了关于小男孩的叙事。小说中对小男孩的性格特征有大量正侧面描写,“他觉得他们不会相信他的。因为他是个孩子。他为自己是个孩子而忧伤了起来。”“你抓住那个家伙后,让我来看看。”“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父亲还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不许胡说’。”这些描写都凸显出了小男孩的机智、冷静、果敢,也表现出男孩希望获得尊重,获得大人的认可的心情。而电影中对小男孩心理活动的描写较少,多是通过小男孩与警察马哲的对话以及蒙太奇手法表现出来的。小男孩与马哲的第一次对话刚开始时,小男孩并没有出现在镜头中,随着谈话的进行,小男孩出现在画面中央,把玩着玩具枪,此处镜头并没有随着说话对象的切换而改变,而是通过小男孩边玩儿玩具边冷静应对警察询问的镜头来暗示他的性格特点。通过与警察的对话,反映出来小男孩超出同龄人甚至大人的冷静与机智。随后镜头拉远,马哲与徒弟以及小男孩和他爸爸在画面中构成了平衡,这也暗示着小男孩与警察同等的“地位”。

《河边的错误》电影海报
电影增加了许亮的“异装癖”。许亮在小说中是一个孤僻的人,他有幻想症,爱好是钓鱼,总是将别人做的事情幻想到自己身上的人。在电影中,许亮是一个有着“异装癖”的理发店店长,因为有人做伪证,许亮以流氓罪被判入狱八年,第七年才被放了出来。电影中,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许亮总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对警察极度不信任。他无数次表示自己不会反抗,直接把自己带走就行。电影中,马哲第一次找许亮谈话时,理发店的镜子呈现了许亮的像,这也是在暗示许亮的另一重身份,也是许亮想要极力隐藏的秘密——异装癖。这一暗示第二次出现在马哲到许亮家里问话,卧室的镜子又一次倒映出许亮的影子。而马哲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发现了许亮的异装癖之后,许亮无法接受自己的秘密被揭开,无法忍受异样的目光,于是在给马哲送完锦旗之后,选择跳楼并坠落在马哲即将开的车上。这一事件自然给马哲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间接推进了马哲向“疯子”的转变。
三、融合与分离:电影与小说界限“之妙”
在改编领域,成功的经验通常被认为是以电影语言阐释文学语言,将电影性附着于文学性之中,展现为更为宽广的影像视野。改编中的忠诚度是指“改编是否成功再现了文学作品的基本故事元素和核心意义”,包括故事情节、思想观念等方面。改编忠诚度的高低也成为部分观众衡量电影好坏的标准。
(一)影视与小说的边界融合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早期对先锋文学的尝试,看似是悬疑小说,实质上悬疑的元素只占了小说的一部分,它的底色是真假、虚实、对错、生死等二元对立,是个体与荒谬的斗争,是探寻生命的意义。在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中,小说并不是单纯作为电影的文本载体,而是为电影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不应当把文学视为可供改编的作品的仓库,而应当看成主题和方法的遗产,看成思维、认识和表现方式的经验总汇。因此电影导演选取部分元素为主题线索,对小说中的人物及情节进行增删,建立新的逻辑框架,最后殊途同归,并获得了作家本人“忠于原著”的认证。由前文所述可知,这一忠实原著的评价并不是片面地指电影对小说内容的忠实,而是对其主题的忠实。可见,媒材与媒介的不同并不影响电影对小说的还原度,相反电影与小说之间的相互转化更体现了两种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相通的妙处。
互文性是指文本间互相影响与互相指涉的性质,当文学文本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时,不同文本间也可以根据互文性来建构故事的网络形态。“互文”概念突出了语言的变动不居的性质。它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意义的可能性,也为影视艺术的表意活动开辟了无限的空间。不同艺术类型所使用的媒材与媒介不同,却可以传达出同样的内容。小说以文字为载体,通过字词句的排列组合,来描写环境、刻画人物形象以及性格特征等。小说中,风景的描写,人物之间的对话,甚至是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可以通过文字辅以读者的想象力表现出来。比如,小说开篇就将线索陈列了出来,并都以代词“他”或“她”代替,读者对于凶手的认定变得模糊,而在电影中,小说出现线索的地方却被导演以柔和的音乐配合阴沉的雨天以及对河流的拍摄这一段空镜头代替,不仅烘托出了整部电影的基调和氛围,也点明了电影的主题之一——河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美术学院]
(本文未完,全文见《中原文学》2024年8月刊)
责 编:祝俊
二 审:海焰
终 审:李纲
签 发:李辉

中原文学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