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作 谈
小说《丛林河马》创作谈
◉张沅
“丛林河马”是我小时候玩过的过山车类的娱乐设施,它起伏不大,速度很低,车的样子是五颜六色的河马,在公园最深处的草叶和低矮的灌木中,播着欢快的儿歌穿梭。我的家乡在内蒙赤峰,一个边远的北方小城。2000年左右,互联网智能设备不像现在这样普及,也没那么多豪华的大商场。小孩子能玩的地方无非是新华书店、公园、小小的动物园或者爬爬红山南山。现在想想有些单调,但小时候觉得公园里涂鸦的画板,聚满小朋友们的沙堆,玻璃弹珠和十块钱两圈的丛林河马,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
去年夏末,我在老家的街道游荡过许多时间。偶然又来到小时候总去的长青公园,跳舞下棋的老年人替代了小孩子们,曾经的动物被迁去了新建的动物园,虽然公园内的娱乐设备更新、更漂亮,道路绿化也都井井有条。但我总觉得,有许多东西在用一种逐渐崭新的方式老去。它变得更规整、更现代,但部分独属于它自己的质地,像模糊的回忆一样,被某种更高效、更迅捷、更工业的要求置换了,“丛林河马”也是这样被“抛弃”的设备。
硕士毕业时,就业市场低迷,身边许多非常优秀的同学朋友,都很难找到匹配自己理想的工作。我们不断压缩自己,不断“内卷”,用一个又一个光鲜的成就和履历让自己被看见。我却觉得,恰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时代在以我们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庄严地前进,我们追求崭新、快捷、高科技。这也许是人类科技发展的趋势,但不该作为单一的,我们认知和衡量世间万物的唯一准则。我想写的是在变迁和发展中被淘汰的东西,不那么耀眼的一切,它们也许衰老、灰败,也许正生锈,也许早该被抛下,但它有它的不可剥夺和替换的价值,正如我们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评价废弃物:“废弃物作为一个‘反向的存储器’,不仅是清理和遗忘的标志,它也是处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的潜伏记忆的一个新图像,一代又一代地坚守在在场和缺席之间的无人之地。档案和垃圾之间的界限如此看来完全是可移动的。”我借“丛林河马”写一种变形的珍贵回忆,它是借助这个被抛弃物所呈现的,它也许代表一种该被看见和珍视的焦虑,一种不够完美的价值,一种独特的,需要被唤醒的记忆。它有缓慢的速度,斑驳的涂层,略带幼稚的儿歌,也许它不够先进,不够时髦,但它需要是它自己。借助这篇小说,我也在回应和处理自身作为青年人的焦虑,比起某些光鲜的前缀,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某种视角,去发现和面对“不够优秀”但“足够完美”的自己。
责任编辑:杨阳

作者简介:
张沅,蒙古族,1998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南京大学创意写作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在读。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见《莽原》《草原》《科尔沁文学》等。

节
选
丛林河马
◉张沅
傍晚,天空在灰暗中更灰。风穿过积满灰尘的纱窗,像捻了口水的棉线挤进密密麻麻的银针,刺痛窗帘,离开它,拂过屋内陈设在各自位置的哑巴物件,留下气味和尘土。树枝上的人稍稍迟钝,但动物本能仍准确辨别出同类慌张奔跑的步伐。捕食者在等待,树枝摇摆,心跳加快,大地被从更深处点燃深埋的引线,爆炸,泥土弥漫。随后,突然地,下起雨来。
雨点砸中里外两层的厚玻璃,极不情愿滑落。窗户没关,有些雨掀进屋内,把窗台整齐码着灰尘的课本和参考书打湿,略略擦去它们身上因常年日光照射而褪出的淡斑。风擂着鼓,把开着的窗户一遍遍推向静止的白墙。吴彤从屋里快步搓着拖鞋走出,下雨了,快把窗户关上。她是我妈。
就这样呗,没事。我回答。她啧了一声,显然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记忆里,赤峰的夏天从来不热,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最热的,八月末也不见凉快。家里空调太老,只吹热风。我穿吊带,家里能开的窗户都敞着,还是热,嚼冰块也不管事。好不容易下雨了,凉快凉快,我又补了一句。她回身往厨房走,薅了两颗葡萄吃。小蜜蜂,绿色的,薄皮儿,吃起来像嗑瓜子,特脆。忽然打闪。
把灯关上吧,我边说边起身。雨比我更快,像为敲着一面破锣生气。高考后,我们搬到二手房里。小区老,楼建得又矮又近,晚上开灯不拉窗帘,对面看得一清二楚。楼后的人家总光膀子躺着玩手机,俩小孩,小的跟他两口子一屋,大的自己住。前面四楼那家男人做饭,也光着,孩子住后屋,正对着我,后半夜还亮着灯,不像高中生,高中生没有暑假还学到后半夜的。防着我夏天不穿裤子在家里走来走去,吴彤把家里所有窗户都挂上窗帘,厨房也不例外,本命年避星星正好,她这么说。我把屋里的灯都关了,窗帘敞着,窗户也打开。
过来看闪电,我喊她。
她走到窗边,小小的,挺暖和。有东西捕获我,以其蔓延布满沟壑的上牙膛的奇异瘙痒而被舌头迅速觉知。我生在只剩颜色和干瘪脉管的蒿草地间,它滚动,蔓延,在任何地方扎根,像包裹婴儿的粗布床单般包裹着草原上一个个散落的边城。我的血里也流着蒿草,我们都是。每个与它有关的,它的子民,都会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患上难以回避的过敏症状,这是我们的成年礼。我又打起喷嚏,也许是伴随雨水的冷空气,或成千上万个拥有名字的正搭着这趟迅猛的班车的过敏原,但我明白,这是我又回到了摇篮。
不会要地震吧,她说。也有可能,周玥家最近刚震完,我说。周玥是我读研时最好的朋友,她刚入职不久,我们却几乎断了联系。吴彤叫了一声,她家没事吧。她说都没事,我回。地震是被束之高阁的词语,在这片土地少见得可怜。像房梁上阴干的腊肉,占据着阴暗、灰败和尘土,一些被遗弃的蛛网,又在这之间,在它奇异身体的内部,将自己从内而外悄悄改变。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有次地震吗,长这么大就那一次。我看着窗外,余光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对面也站在窗前的两个小孩。记得,当时你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她笑。当时好像是在商场里吧?我问。旁边是电梯口,我堆委在女模特脚边,地板很滑,反射着吊顶的圆灯。我在起伏的地面滑动,好像屁股下坐了一双没开刃的冰刀,女装模特也逃着,用她们光滑身体的某个侧面,有的摔掉头,头就跟着身子一起滚动。没人叫喊,大家沉默又慌乱地被投入冰封的河,耳鸣证实了水的侵入,从嘴和鼻孔,我们都成了河中的哑巴。
在咱家旁边,好像是个商场吧,我问。欸,叫啥来着,她说。雨越下越大,闪电在两幢高楼间,摁快门般,给城市一张一张拍着相片。蓝岛大厦,想起来了,叫蓝岛大厦,三道街在北方商场旁边。蓝岛大厦,我头一回知道这个大厦的名字。
最早的头道街就是赤峰城区,后来才有了二道街三道街。街道像放置在培养皿里的菌丝般,本能地避开河道与山脉,尽情繁衍。我在三道街北方商场临街的顶楼里游荡了很久,有关白墙和渗透得很快的水彩笔。我画出自己,不规则圆的脑袋,线条的四肢和两个点,我的眼。一条弯弯的波浪线,是我的嘴。后来掉了块墙皮,正在我的嘴上,弯弯的波浪线多出个古怪的白点。多像你的牙啊,爸爸说。我在那个嘈杂的大屋子里换下第一颗牙齿,把它扔在吃空的两块钱的维生素B小药瓶里,放在家里的最高处。掉了的牙要扔在房顶上,剩下的牙才能向上长,妈妈说这是规矩。
我从妈妈的自行车后座跳下,先快速打量了一遍长青公园的门口。卖气球的摊位在,东西没变,喜羊羊、哆啦A梦、奥特曼等等。大象气球,我最喜欢的,十块钱一个,妈妈说那东西没用,不买。卖吹泡泡的摊位在,他摊子上摆着“竹蜻蜓”和“机械青蛙”,竹蜻蜓只要两块钱,一根棍子一片螺旋桨,双手一捻,一松,它刺溜就飞了,悬在空中,再落下。我有两个,爸爸给我买的,爸爸总是更好说话。门口左边是卖饮料和台湾烤肠的摊,这个我放心,每次走出公园门,只要我稍稍央求,无论和谁一起,都能得到一根台湾烤肠。还有卖小鸡的,老远就能听见叽叽喳喳的声儿,前面有块牌:艺术小鸡。黄色的绒球挤在白色的泡沫箱里,像块会动的毯子。我养过几次,没几天就死了。爸爸说不能买染色的,普通黄色的更好养活。我跟妈妈逐个把摊位看了一圈,也许这次能买个小铲子,红色的,绿把儿。这样我就又能跟林慧挖沙子,我问妈妈能不能买,妈妈说不能。我猜也是,跟妈妈要什么都很难成功。我跟林慧约的是三点半。
在城堡的地下室第一次见到林慧。她趴着,我也趴着。脸对脸,像两个还没撞上的火车头。你是谁,我问她。她吭叽两声,没说话。这是我的城堡,你出去,我说。我从那边进来的,我自己挖的,她说。那也不行,我先来的,我说。城堡塌了,她大哭,我有些不知所措。她妈妈很漂亮,蓝裙子,白高跟鞋,长头发。跑来,蹲下,把林慧的脸擦干,抱着她说些什么。我站在原地,扑拉了几下衣服上的沙子,盯着脚尖看。黄色凉鞋,鞋里全是沙子,沙子黏在脚趾头缝里,有点痒。裹了沙子的脚被我看得越来越热,烧起来一样,眼泪落下去很多,火就熄灭了。
我叫林慧,你别哭了,咱俩再重新挖。抬头看,林慧妈妈蹲在她身后,推着她,冲我笑。面前的是林慧,脸有点红,清鼻涕流过嘴巴,她抬手抹了把鼻涕,抹在裙子上,看着我,双马尾上绑的是樱桃小丸子的头绳。你的头绳挺好看的,我说。我俩成了朋友。我们在沙地上建造属于我俩的城堡,刚刚能容纳我俩的头。又见面了,我趴着说。林慧走时拆开自己一个辫子,把樱桃小丸子头绳放在我手心,下周六我还来,咱们下午三点半在长青公园门口见,行不。我郑重地点点头,把樱桃小丸子头绳攥得紧紧的,我像《美少女战士》 里的水冰月,或是 《东京猫猫》里的桃宫梅,樱桃小丸子头绳是我和林慧变身的魔法武器。
长青公园中间有座假山,红色。周围是水,前后各一座小桥。假山里有俩山洞,一个大,一个小。小的隐蔽,我和林慧把它用作秘密基地。假山最高处看,前面小桥对着儿童乐园,里面有沙地、健身器材、充气城堡。儿童乐园旁边是聊斋宫,里面有鬼,也要门票,没去过。孔雀园在聊斋宫和儿童乐园中间,散养着几只孔雀,尾巴挺秃。两只会开屏,一只绿色,一只白色,妈妈给我和白色孔雀拍过照片,它有点不乐意,我也是。孔雀园里还养着老鹰,关在笼子里,挺臭,总盯着我。我想把它放出来,像公园里的麻雀,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但它笼子上了把大锁,我和林慧用砖头砸,没开,只在黑色锁身留下几条砖红色的花纹。像老虎,林慧说。红老虎,我说。
后面的小桥对着百鸟园,散养着各种鸟,鸳鸯、天鹅、黑天鹅,还有挺多我叫不上名。再往那边关着狼和猴子,还有鹿,我喜欢鹿,它们眼睛大,湿漉漉地看着人。鹿喜欢吃胡萝卜,我总带胡萝卜喂它们。有一头鹿从来不吃我的胡萝卜,也不凑在铁笼子跟前,远远地看,眼睛忽闪。被它盯着挺不自在,好像我是片叶子,或是突然需要展开的树,沙果树,或是苹果树、梨树。风雨和太阳在我身体里一瞬间划过,我探向沙粒的土壤,形成自己的根,又朝向丰沛的雨水,变成自己的叶,在北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回应它的目光,最后结出甜蜜的果子,被它整齐的门牙咬得迸出汁水。狼总是走来走去,垂着尾巴,很快地踱步,焦急地溜着铁笼子的边,大大的尾巴一扫一扫,狼笼子最干净,几乎没什么味。我也想喂狼,但不知道用什么喂。有次我跟林慧跑到公园门口买台湾烤肠,热腾腾的,特香,我一路举着跑回去,想给狼吃。但狼笼子的铁丝网太密了,我俩把烤肠咬碎往里扔也扔不进去,后来我俩蹲在狼门口把烤肠分着吃了,我吃得少一点。因为是你想喂狼的,林慧说。猴子很吵,上蹦下跳,它们的手和我的手是动物里最像的,只是手掌更长,还脏兮兮,脚也很像手,真奇怪。猴子最好喂,它们什么都吃,还会抢,伸出笼子把你手里的香蕉苹果抢走,还抢牛奶饮料。坏,林慧说,猴子是最坏的。我也不喜欢它们,猴子的笼子是最脏的,臭气熏天,他们三五个靠在一起,似乎在密谋着些不可告人的坏事。
儿童乐园门口有个小摊儿,我俩总去。老板又高又瘦,皮肤特黑,坐折叠板凳,膝盖和肩膀差不多高。他像只竹节虫,我说。每次来长青公园,把假山、动物们和儿童乐园都巡视一遍,我俩就神秘兮兮地笑,走,上竹节虫那儿去。竹节虫摆手工摊子,能给白色的卡通人涂颜料,做沙粉画,流沙笔盒,变色马克杯。他那儿啥都有,但都挺贵,没有爸爸妈妈领着,我俩玩不起。最开始我们站着,有点看不真亮,就蹲着挪到摊子旁边,别的小孩趴在桌子上做手工,我俩趴在桌子上看他们做手工。竹节虫不赶我俩,也不正眼瞅我们。我俩有点怕他,跟他离得挺远,也没说过话。有次突然下大雨,摊子上的大人小孩都跑了,竹节虫噌地站起来,伸着他拐棍儿似的长胳膊敛摞桌上的东西。我跟林慧也一人拿几个,学着他的样子收进小车里。我们仨还没收完,雨就停了。他啧了下,把手里的东西一股脑儿放到桌上,回身儿抽了张涂色画递给我俩,画吧。我俩没钱,林慧说。不要钱,送你俩的。竹节虫边说边把手插进裤兜,捅咕了两下,只把手指塞进去了,半截手掌还剩在外面。我和林慧说谢谢叔叔,他说别叫叔,叫哥。
竹节虫旁边的摊子卖小动物,仓鼠、花枝鼠、金鱼、小兔、花狸棒子,种类很多。摊主是个胡子比人还高的老头,白胡子,白褂子。无冬历夏地白在那儿,冬天是雪人,夏天像老冰棍儿。看完竹节虫的摊子就去他那儿看小动物,他总笑眯眯的,爱说话。只看不买也不赶我俩走,人少时还拿小兔出来给我俩摸。我喜欢仓鼠,林慧喜欢金鱼。我说仓鼠又小又毛茸茸,林慧说金鱼颜色多,尾巴像云朵。白胡子老头笑了,还是小娃娃啊,喜欢的都是这些不通人的笨玩意。啥叫通人的,林慧问。就是有灵气的,早年有,现在不太好见咯。老头捋着胡子,眯着眼,拿起旁边的玻璃杯喝茶,又用手搬着跷起二郎腿。你快说说,啥东西呀,我央求。蟒蛇呀,黄鼠狼呀,都是能成精的,你们见着要客客气气地把他们请走,可不能冒犯了。老头身子前探,伸出一根手指点着空气,他骨头明显,只裹着层透明的皮。嗐,这我知道,我奶奶也给我讲过。林慧拉长了语调,她总喜欢在得意时把语气词拖长,好像永远到不了头儿一样。
不知走了多久,速度快得不能再快,一切被向后拽去,时间却很慢。回家的高铁,我飞驰过大片大片的玉米地。过了承德,云就突然松了口,一朵一朵飘在天上,边缘清晰。旷野平得叫人忍不住往远看,目光不可及的终点,还是模糊得只剩颜色的玉米地和锋利的白云。旷野有风暴降临,晴天镀金的白云间,承受不住乌黑颜色的云朵向大地伸出稠密的根系,它们纠结缠绕到没有彼此,却丝丝分明,好像天地间缝了一块灰蒙蒙的棉絮。
毕业已三个月,比起习惯吴彤,我倒先习惯了家里的干燥天气和长久盘踞在鼻腔的清鼻涕。沙蒿过敏,绝对是,吴彤这样说,当时为了治风沙引进的,现在控制不住了吧,这叫外来物种入侵。我倒觉得挺好,过敏把我和家乡稍稍分开,始终提醒我这个外来物种,别过早地成功入侵。吴彤放暑假,我放假。我俩成了凉快天的街溜子,天热时不出门,窝在家里看剧,这叫宅女,我教吴彤。早知道我高中不学了,念完研究生又回来做社会闲散人员,还不如高中就开始,你说说,少走十年弯路。我搂着吴彤的肩膀。吴彤笑了,我看也是,省得教你了。我们从六西街开始走,路过万悦城,进去买两瓶进口饮料,我喝一瓶半,吴彤半推半就喝半瓶。又喝饮料,这都是添加剂,还胖人。没事,主要胖我,我说。明天还买上次那个吧,这回的不太好喝,吴彤说。她咂咂嘴,仰头把瓶底的又倒倒。再往前路过女人街,整条街全是金店,周大福、周大生、老凤祥、老庙、百泰、赤峰金店……我俩一个一个挨着逛,我进门说自己要结婚,买三金,店员就热情相迎,把店里最贵最粗的链子手镯都给我试一遍。我戴上端详两眼,随便说个毛病,摘下来递给吴彤,你试试。吴彤则是说说优点,我看都挺好,要哪个都行。你俩是姐俩吧,店员猜测。吴彤不好意思地笑。她是我妈,我回答。店员夸赞吴彤年轻漂亮时,我一手拿起柜台上的包,一手拽着吴彤胳膊,礼貌笑笑,这个挺好,再转转,要买的话联系你。整条街逛下来,少说加十个店员的微信。
小学开始,吴彤带我逛街。出门前叫我记好话术,她试啥衣服我都说不好看,她则故作为难地表示喜欢,这样能讲价,吴彤教我。承天商厦是我俩的最后一站,我视自己当天的表现而选择央求塑料珠子手串儿,还是蕾丝发卡,当然还有一楼的冰糖葫芦和台湾烤肠。要是她心情好,或是我最近成绩不错,被班主任表扬,我就能拥有一个招财猫。招财猫在承天商厦二楼东边的拐角,两层玻璃柜台,摆各种各样的小瓷猫,指甲盖大。十五块一个,要几个都行,能编手链,老板说。她是个我奶奶年龄的人,戴小眼镜,架在鼻尖上,看东西时抬着下巴,嘴唇微张,嘴角向下撇。这个绿色管学习,粉色是爱情,黄色的是友情,黑色的啥都管,你拿个绿的吧,这个,怎么样,多好看。她边说边拿出来四五个小瓷猫,一排摆在玻璃柜上,我只比柜子高一点点,正巧能凑着眼睛看。我趴着端详玻璃柜上的小猫,圆滚滚,花脸,笑模样,肚子画着小花,不一样颜色。妈妈帮我选了最圆的,我也喜欢,店老板拿根红绳在我手腕比量下,两个手掌对到一起从手掌捻到指尖,小猫脑袋穿过余出的线,底座上一片圆的七彩透明塑料片,拿打火机一烧,一摁,就做好了。我有很多串儿,各种颜色,大的小的,小猫小狗,小猪小虎。它们在洗手弄湿了手腕的瞬间,在姑姑从北京带回来芭比手链时,游泳前,或是某个起晚了的早晨轻轻消失。隐藏在柔软的帆布袋,磨破了胳膊肘的羽绒服兜,装满彩色玻璃弹珠的茶叶盒里,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中,像细小沙土那样,透过筛孔,散落到我不敢回头的,潮湿如呢喃的记忆深处。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莽原》2024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杨阳
《莽原》2024年04期目录
【总第253期】
叙事
短篇小说
夏尔巴女人▪陈家萍
明天到独立镇▪王西愚
丛林河马▪张沅
划火柴的男孩▪欧野
朱 鹮▪吴祖丽
祝红丽回来的那个早晨▪何春花
金 距▪胡炎
中篇小说
风入松▪阿英
劳伦斯学坏指南▪孙鹏飞
伞 仙▪庞加文
新乡土
清嘉巷(小说)▪戴艺贝
墙头上跑马(散文)▪黄风
老宝窝与稻草垛(小说)▪王明宪
随笔
要有光▪ 赵树义
壬辰年纪事▪曹亚瑟
不尽长江
——杜甫晚游录▪王猛
吟咏
流水辞▪古司拨铺
那时我们习惯梦想▪杨永兴
在中原行走▪邵超
向未诗歌▪向未
没有腹稿的曲音▪海月
知见·文学讲稿
故乡何以文学▪梁鸿
订阅方式
全年共6期,共90元。
1、扫描下方收款码直接订阅
(付款时请在备注里填好姓名、收件地址和电话)
首推订阅方式

2、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36-48
扫描下方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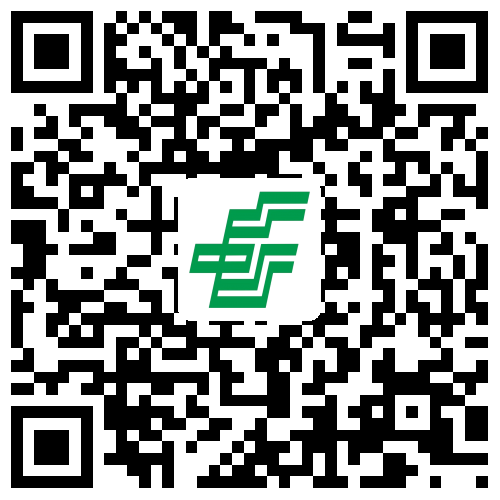
3、扫描下方二维码淘宝订阅

4、直接联系杂志社发行部或编辑部订阅,
联系电话0371-65749451,15225093800
《莽原》杂志社联系地址:
郑州市经三路北段98号
电话:(0371)65749451 65749452
投稿邮箱:
mangyuan6@sina.com

《莽原》电子版可通过
博看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阅读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莽原》公众号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