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作 谈
我的凉州,我的大漠黄沙
——《凉州曲》创作谈
◉李剑鸣
《凉州曲》是我这两年最想写的那种小说,也是最接近我内心对小说艺术认知的一个文本——像梦一样迷幻,光怪陆离又五彩斑斓,没什么现实的逻辑和道理,却按照某种内在的规律肆意生长。关于这个小说的写作动机,大概是某夜醉酒,梦里大漠狼烟,孤城一片,残月挂在远山尖。石头干渴得发疯,叫嚣着要举旗造反。人没水喝,只好饮酒解渴。喝饱了就骑着骆驼招摇过市,像百灵鸟一样用沙子洗浴。
我生活在甘肃东南部,长江与黄河流域交界的一座最不“甘肃”的小县城。小城四面被山围成一个铁桶,这些山都有两张面孔,向阳坡黄土斑驳,干旱雄浑,背阴处林木葱郁,有南方气韵。在大山的褶皱里,夹着许多古老的村落,每个村落不远处的某个险要山头,必定会有个堡(bǔ)子。堡子是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墙围成的四方,墙高三丈有余,厚约丈许,传说大都落成于清同治年间,为防土匪掳掠。这是小说里土堡的原型。
写写改改,前后一年多,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从我近两年的写作来看,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怪异诡谲,字里行间尽是荒唐。大概一个人老实久了,总想做点出格的事。小说里的胡古月和橘子也是这样,他们要做出格的事,要私奔,要去新疆种瓜种菜种葡萄,结果迷失在荒漠里,见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和事。小说发表后,有人问我,这个奇怪的小说,你想表达什么?我只能说,我想表达的都在那个近三万字的文本里,如果能用三百个字说清楚,我会尽可能地去避免用到第三百零一个字。
我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大都是胡古月、橘子、马大力、陈猴这几个名字,一来给人物取名字实在太难,取一个合乎自己心意和人物心意的更难,这个难度不亚于再写一篇小说;二来仔细想想,写小说这么多年,我始终只是在写那么几个人而已,他们不是正儿八经的人,大概也不喜欢正儿八经的名字。
作为甘肃人,我至今没去过河西一带,没有亲见过茫茫戈壁和大漠黄沙。但我知道,我所写下的是属于我的凉州,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个凉州,也是属于我的白草黄沙,干渴焦灼,杀人如麻。
责任编辑:刘钰娴

作者简介
1988年生,甘肃礼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作品50余万字,曾获莽原文学奖、梁斌小说奖。
节 选
中篇小说
凉州曲
◉李剑鸣
一
橘子说,男人没有胆子,就像公牛没有犄角。她说的那种牛叫骟牛,我见过,两只牛角像两截被齐根砍断后开始腐烂的树桩。说这话的时候,橘子手里正拿着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我不知道做封面的牛皮来自骟牛还是牯牛,只是狠狠地点了点头。我承认,我有一身好力气,但总缺少一点胆气。
第二天黎明,雾气散尽,我背着我爸留给我的那只军用挎包,在城门洞里与橘子汇合。挎包里有几张干透了的大饼,一只打火机,一把瑞士军刀,一支强光手电。我们要去新疆,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种瓜种菜种葡萄。橘子说有一种人,背个挎包就去拉萨,一路上磕长头,风餐露宿;我们没有信仰,不用磕长头,但要孑然一身。她把那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塞进我包里,抓起我的军用水壶灌了一大口水。我看到水珠顺着她苍白的嘴唇流下来,滴在红色连衣裙的第二个扣子下面。
我们出了城门,沿着公路一直往西走。天还不怎么热,五月的太阳像一只电量不足的白炽灯泡,忽明忽暗。路边上,大片大片的洋槐花开得很疲软,并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我们眼睛里闪着光,一边想象着新疆的样子,一边唱着歌。两个钟头以后,歌声渐稀,话也少了。中午,我们从一座光秃秃的山上顺着盘山公路下来,橘子坐在一棵树下一动不动,四肢松松垮垮,像一摊子烂肉。她把军用水壶里的最后一滴水咂摸干以后,说什么也不走了。我看到她的脸红得发紫,眼角黏着几粒泛黄的眼屎,嘴唇上结满干痂。
我站在旁边,撩起衣摆为她扇凉。
她说,渴。
我说,咽口唾沫吧,先垫垫。
她咽了口唾沫,说,还是渴。
我说,再咽一口。
她的嘴巴扁了扁,说,没了。
我爬上一个高一点儿的山包,四下里望了望,前面有个村子。村子里没什么人,好些门上都落了锁,几条癞皮狗在小巷里无精打采地转悠。我来到一所破落的院子,跳过墙,看到院中的太阳能板发出刺眼的光,热水架上的铁壶锈迹斑斑。我干咳一声,突然不知从哪儿冲出一条狗来,对着我狂吠。那狗瘦巴巴的,像只兔子。
我掀开抽水井旁边苫着五合板的铁桶,灌了一壶凉水,拿给橘子喝。那条狗一直追着我咬,我瞅瞅四下里不见人影,捡起一块石头,砸在狗的脑壳上,狗呜呜怪叫着跑远了。
橘子喝饱了水,精神好了些。
她说,这么下去我们要累死的,要想办法。
我说,昨夜我想着从家里偷些钱坐车的,但没敢。
橘子哼了一声。
恰好此时,一辆平头卡车从远处开过来。橘子伸手拦车,车停了。车一停下,无数的蜜蜂突然飞了过来,把我和橘子围在中间。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探出脑袋,说别乱动,蜂子不咬人。橘子笑吟吟地走到驾驶窗前,跟司机说话,然后我们就上车了。
车里有四个人,最边上坐的是男人大着肚子的妻子,中间是两个女儿,一个十来岁,一个四五岁,都是脏兮兮的模样。车是开往兰州的,男人说,兰州的油菜花开得正好,蜂子有花采的。再过些时日,等兰州一带的槐花落了,便一路往北去。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并不说话,只是明亮的眼珠子在幽暗的驾驶室里不停转动,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目光在你身上摸来蹭去,像把刷子,让人浑身不自在。我和橘子脚对脚坐在驾驶室后面的卧铺里,汽车在望不到尽头的柏油路上喘息。
日头偏西的时候,车过了定西,便走走停停。放蜂人四处查看地势和植被,寻觅放蜂的好去处。后来,车子停在一片碧绿的山谷里。天色已晚,放蜂人有意留我们过夜,并且相帮着安顿下来。山谷里的槐花将开未开,一条小溪潺潺流淌,放蜂人傍溪而居。三座帐篷搭好后,男人从车厢里搬出一个鸡笼,从鸡笼里倒拎出一只白鸡公,斩了头,以血祭祀山神和土地。鸡血滴落在杂草丛中,瞬间变成了暗黑色。鸡是吃死蜂和杂草长大的,鸡血里有蜂蜜的味道。
“放蜂人和蜂子一样,一年到头追着花儿跑。”男人把黄表纸点燃,顺势给自己点上一根烟。
夜里,放蜂人用牛粪烧锅,水烧开以后,鸡毛煺得很快。放蜂人把鸡内脏挖出来剁碎,拌些剩饭喂狗。那几条瘦巴巴的土狗在车上颠了一天,如今吃饱喝足,便在草地上撒欢儿。
大概九点钟,一大锅香喷喷的鸡肉烧好了,六个人就着干馍吃。山风清冷,四下一片苍茫,寂静如水。我和橘子坐在一个鼓起的小丘上,一直看着月亮升到高处。橘子说,新疆的月亮大概要比这儿的圆吧?我们白天种葡萄,夜里就借着月光酿酒。我打了个哈欠。后来,一大朵乌云飘了过来,四周顿时陷入漆黑。橘子有些害怕,到处乱钻。我们摸黑走下土丘,进了帐篷,橘子说,黑啊,怎么这么黑?放蜂人就点燃了半截蜡烛。太阳能蓄电池里的电不多,放蜂人用得很节省,只给手机和电筒充电,照明就基本仰仗月光。
我们睡在第三座帐篷里,那是放蜂人用来储放蜂蜜的地方。床是两个废弃的蜂箱,上面搭一块木板,睡上去吱吱嘎嘎响。大概新换了地方,狗们叫了整整一宿,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放蜂人不时呵斥几声。
第二天一早,我和橘子离开山谷,顺着公路往西走。临走前,我对放蜂人说,他日来新疆,我请你喝葡萄酿的酒。放蜂人笑笑,说,但是我的蜂子要吃花,新疆花多吗?我想了想,说,多,你秋天来吧,遍地都是棉花。
放蜂人送给我们一块防潮垫,那是几年前在兰州放蜂时,一个骑手路过,在帐篷里留宿后送给他的。放蜂人说,若赶上下雨,可以撑开来,顶在头上遮雨;但是从凉州腹地到新疆,一路都是天干地旱的去处,用不用得着还不好说。他把卷成圆柱状的防潮垫用绳子打一个背带,郑重地挎在我的肩头,就像司令把一门迫击炮交给了一个新兵蛋子。
过兰州后,我们搭过几辆车,都是短途。越往西走,草木越发稀疏,太阳很毒,扁塌塌的群山在地平线上裸奔。橘子看着光秃秃的群山和群山当中高悬的烈日,一声接一声叹息。我们都在不住地回头,希望能有顺路的车开来。可惜,这条公路上车少得可怜,偶尔有载满牛羊的卡车疾驰而过,却不搭理我们,只留下一股腥臊恶臭的热风。
那个晌午,地平线上出现一个黑点,在蠕动。近了才发现,是一个戴着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骑手,风尘仆仆地骑一辆单车。骑手走近后,橘子问他有没有水喝。骑手撑住车子,从后座上的行李包里翻出一瓶矿泉水。橘子喝了一口,笑了。她问骑手要去哪里。骑手说没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天当棉被地当床,走到哪儿是哪儿吧。橘子问你的车能带人吗?骑手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说只能带一个,重了不行。
橘子决定坐车,坐自行车,苍蝇肉也是个肉,总比走路强吧。她问骑手沿途的地名。现下是兰州境内,再往前走,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是武威、张掖、嘉峪关、敦煌、哈密、乌鲁木齐。我说,我去哪里找你?橘子想了想,说,你肯定能找到我的。
她郑重地告诉我,那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种植葡萄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还有葡萄酒的酿造方法以及书页里夹着的几块零钱。若是到了新疆,那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还有还有,我想用它为你写诗来着,我写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是我记不起‘浪’字和‘漫’字怎么写,就用拼音代替了。”她看了看天,天上有些抹布样的云朵。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皱巴巴的塑料袋,把笔记本包好,塞进我的挎包里,并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橘子说,没事,你说吧。
我想了想,说,我爱你。
橘子点了点头,跳上了自行车后座。车子晃动了几下,她急忙圈住了骑手的腰。骑手使劲蹬了几脚,橘子的背影被太阳光拉长,并且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公路尽头。
橘子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日头很大,我沿着河谷往西走,出了兰州,走进了戈壁滩。干燥的风吹着骆驼刺沙沙作响,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一些白色的星星点点从一面山坡缓缓移到另一面山坡,我知道那是羊群,并且隐约能听到牧羊老汉的吆喝。走近了,我看到那个穿着蓝色大襟衣衫的老汉,正盘腿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他看到我,把羊鞭甩得啪啪响。这个季节的凉州腹地,连石头背面的苔藓都被晒干了。河水瘦得可怜,抬脚就能跨过,但却清澈见底。牧羊老汉从石头上跳下来,坐在我上游的地方,掬起水喝了一口。我学着他的样子,猫下腰,也喝了一口,河水清凉,有枯草和石头的味道。
我摊开防潮垫坐在河边,从挎包里摸出干饼啃了一口。牧羊老汉使劲咳嗽了几声,也从挎包里摸出一块干饼,嗖的一声扔到河的上游。太阳老高了,天蓝莹莹的,让人心头发颤。他掬起水在后脑勺上粘了粘,又顺带洗了把脸。脸洗完以后,泡得稀软的饼顺着河水流到面前。他随手一捞,便大口嚼起来,水珠顺着嘴角流过下巴,脖颈,流进了暗黑色的胸膛。
我把手里的干饼也扔到上游,蹲下来洗脸。饼子顺流而下,牧羊老汉突然手一伸,饼子便被他捞了去。我吃惊地看着,告诉他那是我的东西。他呵呵呵笑了,这怎么是你的?你的饼上写字了?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没有就对了,这河滩上的石头也没写字,谁的?他凌厉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脸上的皱纹里塞满了狡黠。他捡起一块石头,说,这河滩上的石头,谁拾上就是谁的;然后把石头扔进了水里。
我无言以对,只是掏出瑞士军刀,戳那河底的沙子。
牧羊老汉躺在石板上,跷起二郎腿,把帆布包盖在脸上,少顷响起了呼噜声。我收起刀子,就着河水啃了几口干馍,坐在河边歇了大半个钟头。正在我考虑要不要跟他打声招呼再走时,他醒了。他触电似的坐起来,看着天空发呆,半晌之后,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他曾有过一万只羊,在这戈壁滩贴足了秋膘后,便赶往关外去了。过了半晌,他又说,这戈壁滩上有狼,狼的眼睛是绿的。我问,为什么狼的眼睛是绿的?他说,这是凉州腹地啊,你想想……我不知道想什么,只是脑子里突然出现无数发着绿光的眼睛。我问,再往前走是什么地方?老汉嘿嘿一笑,说,前头的路是黑的,阎王殿还是鬼门关,谁知道呢?我骂了句粗话。
我走得飞快。干燥的风在我耳边嗖嗖响。到处都是硌脚的沙子和碎石,我的双脚火烧火燎地疼。日头在地平线上摇摇欲坠,看不见人也看不见鸟,只有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像秃头上的癞子。我似乎置身在一个骆驼刺和沙丘组成的迷宫里,星辰和日头失去了辨别方向的意义,像一只只失神的眼睛。踩倒无数的骆驼刺以后,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其中一株,干渴,需要水的浇灌和滋润。我的汗毛变成了无数须根,瞬间把满满一壶水吸干,分解,蒸发……
天色将黑,茫茫旷野,四下无人。地势比先前平缓了些,河流干涸,河床裸露。骆驼刺越来越少,脚底的黄土变成了黄沙。走了几个钟头,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人,没有房屋、树木和庄稼。我怀疑是不是走进了无人区,到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被野兽啃了,黄沙埋了。若是橘子还在前面某个地方等我,不知道会不会等到猴年马月?
月亮躲在一大朵乌云后面,但没有要下雨的意思。在我的左边,地平线以上的地方,有几点绿幽幽的亮光。我想到了牧羊老汉说的狼的眼睛,不禁浑身打个哆嗦,脚下加快了速度。地势在慢慢上升,我的恐惧也在慢慢上升,从胸腔上升到脑袋,头发芒刺般一根根奓起。好在这种恐惧只持续了片刻,月亮便出来了,这月亮比我在养蜂人附近那个山包上看到的还大。在这样的地方,在这种时候,月亮升起与太阳升起一样,能给人某种勇气。月亮一出,那些绿幽幽的亮光便消失了。
我把长袖汗衫搭在肩头,我光着膀子,迎着沙尘和热风,最后如一株孱弱的枯草被风吹倒。我趴在沙丘上,沙丘热烘烘的。我咂吧嘴唇,沙尘就灌进嘴里,很涩,根本无法下咽,倒呛了一鼻子的土。天亮了,黑了,又亮了,又黑了,如此明暗交替,如眨巴的眼睛。穹顶上,日月星辰密布,有几粒坠落进无边的黑暗中,剩下的开始颠倒,旋转……我艰难爬行,像只跛脚的沙蜥。天和地粘连一处,像一口浓痰,我黏在其中,像被粘板黏住的苍蝇,无法动弹。我终于挣脱,嗡嗡嗡到处飞,到处撞。我不知这是不是回光返照,但我充满力量。我越过无数的沙丘,脚尖在一丛丛的骆驼刺上蜻蜓点水。
月色中,一面巨大的旗子斜挑在半空,顺着旗杆往下,一座四面土墙围拢的堡子赫然矗立在月光下。我围着堡子走了几步,朝南的门洞里两扇木板门紧闭,从门缝里透出的光照在门口那两个神色肃穆的看门人脸上。他们落满灰尘的脸呈古铜色,杂乱的胡茬子东一荡西一丛,就像戈壁滩上稀稀疏疏的骆驼刺。
“来——者——何——人?”两个看门人举起锈迹斑斑的铁片刀挡在门上,吊起嗓子,用一种唱戏般的腔调质问。
“来者……”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说得出口的身份,“是个瞎逛荡的屁人。”
两个看门人相互看了一眼,扑哧一笑。一个看门人问我,是不是带了信物来?我说没有。那看门人脸色陡然一变,把铁片刀架在我脖颈上,另一个在我身上翻寻。当我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气时,他已打开那只褪色的军用挎包,把里面的物件连同一些馍渣子一起倒在地上:一只打火机,一把在河水里泡过已经生锈的瑞士军刀,半张干饼,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搜寻的看门人捡起干饼叼在嘴里,把打火机揣进裤兜,又把瑞士军刀塞给拿刀的看门人。他倒拎着笔记本来看了看,大概是一字不识,便连同挎包一起扔给我,打个酒嗝,手一挥,示意我可以进去了。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莽原》2024年第05期。
责任编辑:刘钰娴
2024年第06期 总第255期
叙事
中篇小说
昏睡的河流▪罗文
最后的吉卜赛人▪虹宇
短篇小说
魔 塔▪叶子
夜风渐息▪王沛
我妈的婚宴在三亚▪孙小方
溺 鸽▪冯曜
谁是疯子▪翟妍
没有月亮的晚上▪张祥森
城里城外▪刘上下
新乡土
在大冢上(小说)▪王清海
水边生活(散文)▪石泽丰
对岸好似故土滑翔(诗歌)▪黄保强
散笔
采唐・采葛▪朱盈旭
少年姚雪垠▪吴永平
译稿
克洛迪亚和她的患者们▪(美)安东尼娅·纳尔逊 著 杨伟莉 译
吟咏
让画面过上好日子▪谭延桐
故乡,或远或近地徘徊▪徐慧根
你见过这样的大雨吗▪半壁心空
马夫的诗▪马夫
逢秋记▪小语
知见
文学讲稿
非虚构写作与性别问题▪梁鸿
订阅方式
全年共6期,共90元。
1、扫描下方收款码直接订阅
(付款时请在备注里填好姓名、收件地址和电话)
首推订阅方式

2、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36-48
扫描下方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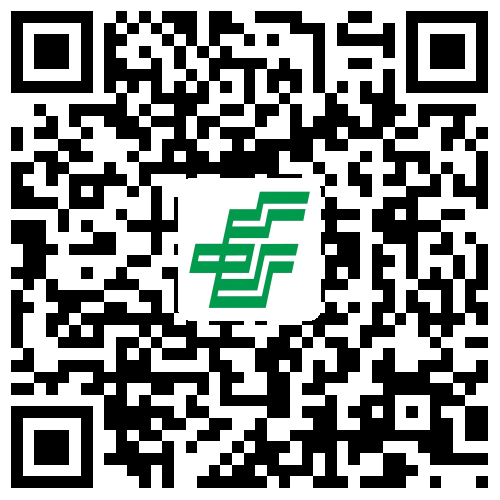
3、扫描下方二维码淘宝订阅

4、直接联系杂志社发行部或编辑部订阅,
联系电话0371-65749451
《莽原》杂志社联系地址:
郑州市经三路北段98号
电话:(0371)65749451 65749452
投稿邮箱:
mangyuan6@sina.com

《莽原》电子版可通过
博看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阅读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莽原》公众号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