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原写作#

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写于2003年,今日看来其中的故事已有些陌生与隔膜。新世纪初的期望、豪情与热烈,矛盾、过往、虚妄投射在一个村庄中,村庄中躁动着权势、滑稽、故事和历史,人们为看似明确的目的而东奔西忙。隔着20多年的时间回头重读这部小说,不可避免要对比近20年乡土小说的写作轨迹。乡土在时代情势、写作者、思想形态、媒介、读者和写作技术的缠绕中已经成为复杂的变体,有过颓败的景观展示,虚张声势驾轻就熟的寓言,也有过廉价的乐观与庸碌的附和,以及时时存续的田园诗和怀乡病。文学中的村庄从来就不是村庄自身,它是经济、文化和审美的复合体,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同的力量此消彼长,文学中的村庄变换着形状和姿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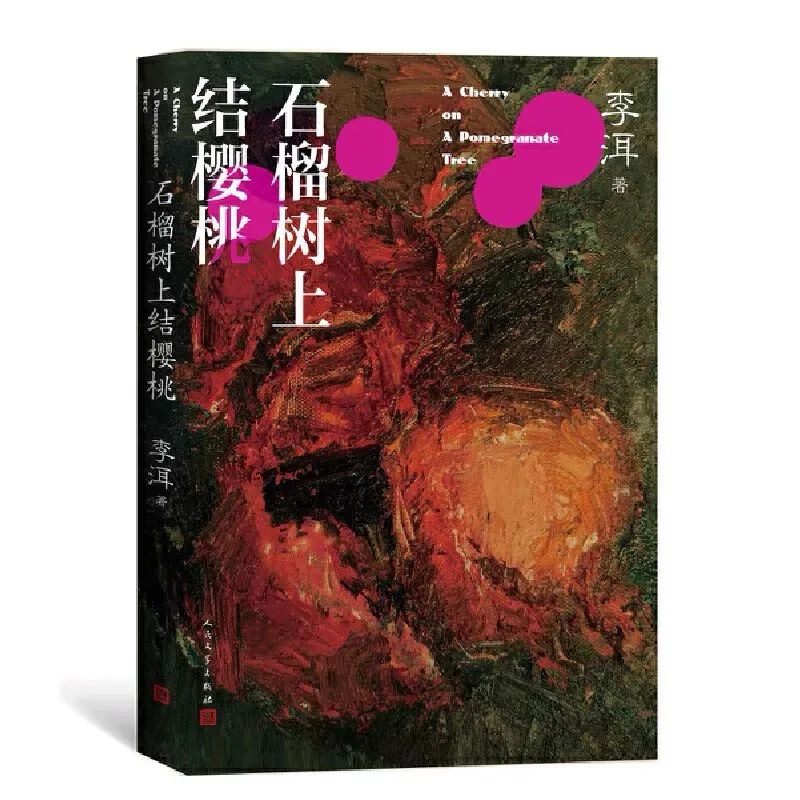
《石榴树上结樱桃》
作者:李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乡村书写基本被锚定在城乡二元结构中。费正清提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个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有势者。学说是对历史和现状的概括和抽象,文学是回到具体的时空和事件,表现和关注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人物的行为、思想、道德和情感。具体的故事和人物命运呼应着其间的不平等与差异,历史和现实不断被投射到文学表达中去,在往复书笺中,基本形成了悲情、怨恨和创伤的基础语调,形成民族国家寓言与神话结构。当然文学也永恒地创造着它们的反面,岁月静好、童年滤镜和停滞的素描,回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家国之外的情感与心灵之需。

太行山下,沁河岸边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主题和讲故事的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镌刻着属于那个时间点上的关切和想象力。李洱在小说自序中确认小说是关于“乡土中国”的表达,两个可以互为定语的词汇组合在一起,沿袭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反复使用的中国描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李洱在写作意图中特别强调了重新书写乡土中国而不是乡村故事的必要性,首先标记出“现在”的特殊性,以示与前人写作的区别,作为严肃的书写者,无法沿袭既往时代的书写范本和新时期以来的种种书写路径,当然也无法完全脱离,这部作品的故事、人物和语言都可以看到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的影子。小说需要借用乡村这个重要空间和故事发生地,因为乡村的“悲喜剧”内在于中国、时代和自我,中国乡村发生的“悲喜剧”冲破现实中的阶层、区隔、地域,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极为重要,“极大地影响着你的生活”。
小说开端即交代了村庄的地理位置,“官庄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王寨村十里,从王寨村到溴水城二十里。” 从莱温斯基丑闻、电影《泰坦尼克号》、娱乐明星和流行歌曲等符号,可以看出故事的大致时间是2000年以后,或者就是作者写作的2003年。尽管有一个真实可感的时空,这个乡村仍然具有装置性。装置性是强调艺术的情境主义,小说没有前情交代与铺垫,就像舞台上的小品,是从女主角孔繁花的丈夫张殿军农忙时节返乡开始的,故事一旦启动就进入喧闹的官庄世界。装置性还体现在艺术的互动性,这一点在作品中体现为随时跳出来的既像叙事人又像小说主人公的评议者,家常般的点评、臆测和随想。
另外装置艺术反对艺术的体制主义,从这个层面来说,李洱小说中的乡村(《石榴树上结樱桃》)、历史(《花腔》)和知识分子(《应物兄》),都具有装置性,指向具体的地点和人物,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生活的常态和话语流赋予了其以势如野火般的自主性,这个自由的王国及其界限又时刻准备从具体情境中抽身而出,发挥自己的装置性。詹姆斯·伍德说:“小说中一个个真实的瞬间,只有一小部分关乎栩栩如生,毋宁说,它们涌向生活的质感也从中抽身而退。” 从栩栩如生的现实感角度,《石榴树上结樱桃》提供了一个整体上看起来略带夸张色彩充满地方风味的小世界,而更应该关注的是作家从前台这个装置世界抽身而退的时刻,因为一个现实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更私人的现实,它拒绝一目了然,“深于谎言,深于啼笑”。
[作者介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本文未完,全文见于《中原文学》2024年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