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那年,郑小驴完成了自己第一篇小说,那时候他周围没有人喜欢文学,他也感到颇为苦闷,只能偷偷地用纸笔写下心中的文字。偶然的机会,他把一篇小说贴在了当时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他一篇篇地写着,走上了文坛。
如今的郑小驴定居在家乡湖南省会长沙,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湖南特殊的风土人情与传说掌故赋予了郑小驴创作的某种地域性。在幼年时代,郑小驴接触到不少具有神秘性质的传说故事,以至于他一直对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感到亲近,也让他写出的小说带有类似的气质。
在象牙塔内安静地教学和写作之余,他常常想要走出这种舒适区,朝向更广阔的世界体验生活。他说:“除了想象,作家一定要走出书房,去更远的地方,更复杂的地方去生活。”为了写小说,郑小驴时常远游,甚至深入一些有些危险的区域,他觉得光有二手经验是不够的,作家必须有独一无二的体验,“要做一个全身都布满雷达的人”。
在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中,郑小驴创造的好几个人物都带有所谓病理学层面的典型症状,是某个意义上的“病人”。比起一般的正常人,郑小驴总是对生活中的边缘人更感兴趣。他认为很多文学素材都诞生于边缘和模糊的地带,正如寒暖流交汇的地方,总是生物繁殖最为旺盛的地方,他也希望自己的小说处在这样一个交汇地带。
本期访谈视频已上线视频号(账号:理想国imaginist),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这是2024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第五期,对谈嘉宾是入围作品《南方巴赫》的作者郑小驴。

2024年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将于10月21日揭晓,敬请期待。
我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
文学奖:《南方巴赫》是你的最新小说集,收录了九篇作品,能否请你简单谈谈这本小说集的创作情况,其中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篇呢?
郑小驴:《南方巴赫》是我这三四年来创作的合集,我写小说比较早,差不多从2007年开始写作。但我写作的速度很慢,所以写了十来年,产量并不高。有时候我也喜欢和自己较劲,对我来说,我写小说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同时也是一种治愈,我比较喜欢安静的地方,写作和孤独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孤独的时候,才能真正面对自我,打开心扉,即使和自己毫无相干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处境也会感同身受,给予理解和同情。
书中的九个故事基本上不涉及我个人的经历,我也很难说自己最喜欢哪一篇。比如说《战地新娘》《南方巴赫》是我个人投入感情和精力比较多的作品。我昨天看到一首诗,我很喜欢,是说“我凭感觉活着,我有很多破绽”。我觉得写小说也是这样,我只能尽力让破绽少一点,我觉得世上不存在完美的小说,只有完美的谎言——每一位小说家都是谎言的制造者。
文学奖:一本小说集的编排是很重要的,我也很好奇你对篇目的安排有没有一些考虑?比如为何会将《南方巴赫》放在第一篇,并且以它为整部小说集命名?
郑小驴:我和我的责编小范老师做过一些商量和权衡,我很喜欢“南方巴赫”这个题目,当这个词语出现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将它用作我小说的题目。另外它是一个中篇,在整个小说集的分量也是比较足,所以我们就很快把这个题目定下来。我平时有一个习惯,会把自己觉得不错的标题记下来,时间久了慢慢积累了一批题目,足够我写很多年了,只可惜我写得太慢了。
“南方巴赫”这个题目也是这么诞生的,我还记得是在云南的某个晚上,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题目,这篇小说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内容的,有点像是“为了一碟醋,专门包了一顿饺子”。另外,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听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巴赫,有时候会单曲循环听一整天,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题目。
文学奖:我注意到你在好几篇小说中都写到一些在精神或者肉体上有缺陷和不足的人物,比如《南方巴赫》《国产轮胎》等,为什么会对这样一群人感兴趣呢?
郑小驴:确实,这本小说集里好几位主人公都有一些病理学层面上的典型症状,相比一般的正常人,我觉得生活中的边缘人更值得关注。我的很多文学素材都诞生于边缘和模糊地带,有点像是地理学里的洋流运动,寒暖流交汇的地方,往往也是生物繁殖最为旺盛的地方。我希望我的小说处于这样一条寒暖流交汇地带。
《南方巴赫》里的艾米丽,《国产轮胎》里的小湘西,某种意义来说,他们都是同类人,打个比方说,就是生活在《天气预报》里的“局部地区”的人。他们当然也都是生活里的零余者,是值得我们关注、同情和理解的人。
作为写作者,我们要在时代中保持某种敏锐性,要做一个全身都布满雷达的人,一旦触碰到某一个敏感点,就会发出强烈的接收信号。我可能就是接收到了这样的信号,促使我去写这样的小说。
文学奖:你刚才说到小说中“零余者”,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为什么你的小说创作也是着力去书写他们?
郑小驴:我倒不是从文学史意义去关注这类人,而是从我出生的环境以及生活中的感受出发。我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特别容易理解他们。或者说,我书写他们是出于我的本能,而不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去关照。
文学奖:我看到有评论者将你的写作定义为“小城青年”写作,你是否认同?
郑小驴:我不喜欢被标签化,写作者,尤其是写小说的人,他需要在一个广阔的疆域中到处探险和摸索,要走出舒适圈。我一直很警惕这类贴上来的标签,说我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写作者。我写过很多农村的题材,也写过小城镇,还写过大都市,我觉得不能说我出了一本什么书,就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这是以偏概全。
作家一定要走出书房
文学奖:《南方巴赫》这一篇有比较强的悬疑感,有一定类型小说的影子,那你对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郑小驴:好的小说是没有这种边界的,很多优秀的小说也有很强的可读性,也可以借鉴类型文学里比较典型的元素。我的小说严格来说不是类型小说,可能我的读者会把它当成一个悬疑推理小说去读,但最后可能会有期待的落空感,某种意义上,我的小说恰恰是反类型的。类型文学一般都会在结尾的地方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阅读的过程像是探案的话,最后就会找到一个答案。但我的小说没有提供这个答案,很多时候采用了留白,这个答案需要读者参与进来,而不是由作者提供的,答案本身就是属于我们人性的、最具有想象力的那一个部分。我觉得现在的读者太期待一个答案了。
文学奖:你的小说也反复出现汽车这个意象,对你来说汽车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对这个意象特别着迷?
郑小驴:是的,我的确对汽车这个意象进行了强化。我记得罗兰·巴特讲过:汽车是工作地点和家的无人地带,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开车去家和公司的路上。这句话我特别喜欢,汽车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物质载体出现的,它承载了我们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很多时候,它也意味着速度和激情,是我们身体对远方的一份想象。
我小时候在农村是很少见到汽车的,而现在私家车几乎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普通家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变化。伴随着汽车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我觉得汽车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缩影和写照。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把汽车作为一种意象,作为一个具体的所指,放进我的小说中。比如《南方巴赫》《国产轮胎》《一屋子敌人》《衡阳牌拖拉机》……都潜移默化地贯彻了我的这种想法。
文学奖:你的小说从一些社会新闻中也汲取了营养,比如轰动一时的吴谢宇案,那么你这些二手的经验与创作的关系是什么?
郑小驴:社会新闻和社会事件给了作家很多素材和养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从中受益。因为社会足够复杂,也足够多元,很多社会新闻都是很好的小说素材。但我们也必须警惕,因为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社会,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得来都太容易了,二手的素材使用太多,却没有自己亲身的感受,就会导致写作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作家在处理类似素材的时候,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进行特殊的艺术化处理,不能生活中发生什么,全部进行一比一的还原。我关注吴谢宇案后,一直很想写成小说,酝酿了五六年的时间。但我不想按照新闻报道的方式来写,更想从作家的人文视角来还原这场悲剧。写《国产轮胎》姑妈这个有洁癖的人物时,我联想到了谢母,人物形象马上就对上了,那种感觉好像在无人区手机突然有了信号。
写作光凭想象力也不行,作家一定要走出书房,去更远的更复杂的地方去过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何为真正意义的生活,就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的生活,没有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很难写出新鲜的有质感的小说的。虽然我们的生活趋于同质化,也越来越模式化,比如我们吃饭点外卖,需要和外卖员接触,似乎都是千篇一律的,谈不上真正意义的交流。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需要突破壁垒,需要越界,需要打破常规认知,全身心参与其中。
我记得大二那年寒假,我没有回老家过年,而是在酒店当服务生。除夕夜万家灯火,落地窗外边的夜空不断绽放烟花,室内推杯换盏一片欢声笑语,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了孤独,一种你和眼前这一切没有任何关联的孤独。每当我想写那种苍凉与孤独时,脑海总会浮现那个除夕之夜,某种意义上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外卖员”,那是属于我独特的生命体验。
文学奖:你出生于湖南,现在也在湖南生活,在你的作品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湖南的地名以及掌故传说,也有人说你的作品里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性,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地域是相关的?
郑小驴:是有关系的,你听我的口音也会知道我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人,这就是湖南的文化特性,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这个骨子里,像血液一样流淌于我的躯体。我的家乡叫隆回,就是歌曲《早安隆回》提到的那个地方,这里是梅山文化的核心地带,有崇巫尚武的习俗,至今流传着各种神秘和禁忌的东西。
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爷爷是一位道士,从小他就会给我讲很多鬼故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听故事的氛围;而我的外公则是一位乡村的基督徒,他会让我去阅读《圣经》,小时候我将《圣经》当成课外读物。这些小时候的经验都会影响我的写作,让我的作品带有一种鲜明的地方特质。
我在阅读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也感到特别的亲切和熟悉,因为南美作家描述的世界和我生活的环境没有任何的隔阂。我理解马尔克斯所说的根本没有魔幻现实主义,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么魔幻。
写小说就像撑竿跳
文学奖:你是80后,这代人如今也是文坛的中坚力量了,你是否觉得自己这代作家存在一些共性?
郑小驴:我觉得共性肯定是有的,我们80后成长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小时候经历了计划生育,到了2000年后,中国加入了WTO,经济腾飞,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我们现在又要面临教育住房等等的压力。这些共同经历赋予了我们一些时代命题。如果要写小说,可能就会把这些背景纳入其中,它就会形成一种共性。
文学奖:你曾是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研究生,现在在一所高校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如今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相关的专业,但是我们又似乎认为写作是无法被教授的,是一种天赋,你是怎么看的?
郑小驴:我赞同你说的写作是非常需要天分的,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教。抛开这一部分不说,写作的基本技法以及阅读鉴赏这些是可以教的。经过专业的训练后,他可能在写作的道路上会比没受过训练的写作者走得更远,这是创意写作有意义的地方。另外,大学的创意写作课堂能够形成一种比较浓厚的文学氛围。我在人民大学学习的三年,最大的感触就是身边有一群热爱文学也很有才华的同学,和他们一起上课、喝酒、聊天,往往能够擦出灵感的火花,感到一种力量在推着你往前走。这个氛围也很重要。
文学奖:你最初不是文科专业,是自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写了这么多年,对写作的理解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
郑小驴:我大学的时候身边没有喜欢文学的人,我读了一些书后就很想写,于是开始偷偷摸摸写小说,写完了也不知道往哪里发表,还要受到周围人的嘲讽,觉得我不务正业。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散步,突然很想写一篇小说,赶紧买了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口气就写了一篇,不知道往哪里投稿,去贴在当时一个文学网站“榕树下”,引起了很多关注,受到了很多鼓励,那是我第一篇小说。有了第一篇,就有第二篇,第三篇……我早期的小说都是手写,我再把它们敲击到电脑里。我就是这样慢慢走出来的,完全凭借自己的感觉,加上我对生活的理解,阅读是我最好的老师,完全没有人引导。
这些年变化肯定有,更多是一种内心的变化,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的理解都在改变。以前我对社会的理解是比较浅的,也比较片面,不够客观。随着接触社会的层面越来越多,我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想的那样。以前的小说肯定和现在也会有区别。作为小说的写作者,应该要站在不同维度去观察社会,这样才能更客观,也更加深刻。
写小说就像撑竿跳一样,要一点点地挑战自我,不论是从语言、题材还是具体的表现手法,都要对自己提出不同的要求。说实话,我早期写的一些东西,现在肯定是不愿意写了,那个难度已经越过了,再去写就好像是降维打击一样。我现在要给自己设置更高的门槛,需要有更高的挑战。
文学奖:那你现阶段从创作来说最想挑战的部分是什么?
郑小驴:我现在特别想写1980年代到2010年前后三十年的变化,很想把这个时代当作一个丰富的横切面,用小说的载体来呈现。刚才我们聊到一代人的共性,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也有三四十岁了。在这个时代,走过这三四十年,经历了很多事情。如何用文学这样的形式去回忆它,呼应它,是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要正面去回应一些社会问题是很困难的,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数字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资讯获取非常便利,但这种便利性有时也会反过来加深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比方互联网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偏好推送信息和产品,人们也更愿意去阅读和自己既有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东西,从而强化了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信息茧房,最终作“茧”自缚,不愿意接受不同声音。今天的人都戴着一副数字的放大镜,能看非常清晰的局部和细节,却更难把握事情的全貌。作为小说写作者,应该努力跳出来,避免我们成为算法的俘虏。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共同发起。公正、权威、专业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诞生时确立,并将一以贯之的原则。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华语文学领域首个为发掘和鼓励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由商业品牌与出版品牌联合创立的奖项。这一奖项的设立,也是为了让大众真正感受到“读书,让时间更有价值”。
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不仅关乎作品的艺术价值,更深刻影响着文学的走向和未来。一部作品的语言表达是否扎实、特别?内容有无直面人生?作者心智是否足够丰富,能否在消遣之外提供某种生活中缺失的教益?有没有强烈的小说意识,即人类存在之痛苦、这个时代的感觉,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趋近?从中能不能看到新的东西,有没有令人惊叹、佩服的创造力?对于未来十年的中国文学,作者及其作品的存在,是否具有某种好的引导性?……
本届评委团成员陈冲、骆以军、双雪涛、许子东、张定浩(按照名字拼音排序)经过热烈讨论,依照多数原则表决,评选出五部作品进入决名单:


(点击图片 ↑ 购买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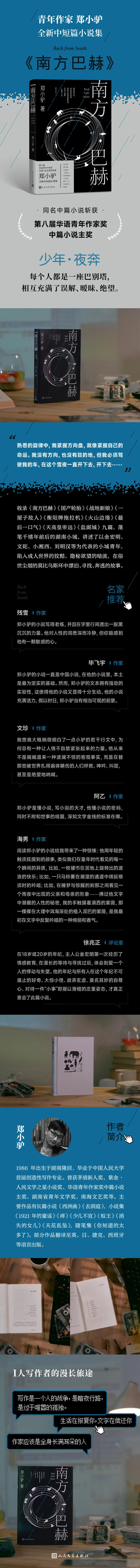
稿件初审:张 瑶
稿件复审:张 一
稿件终审:王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