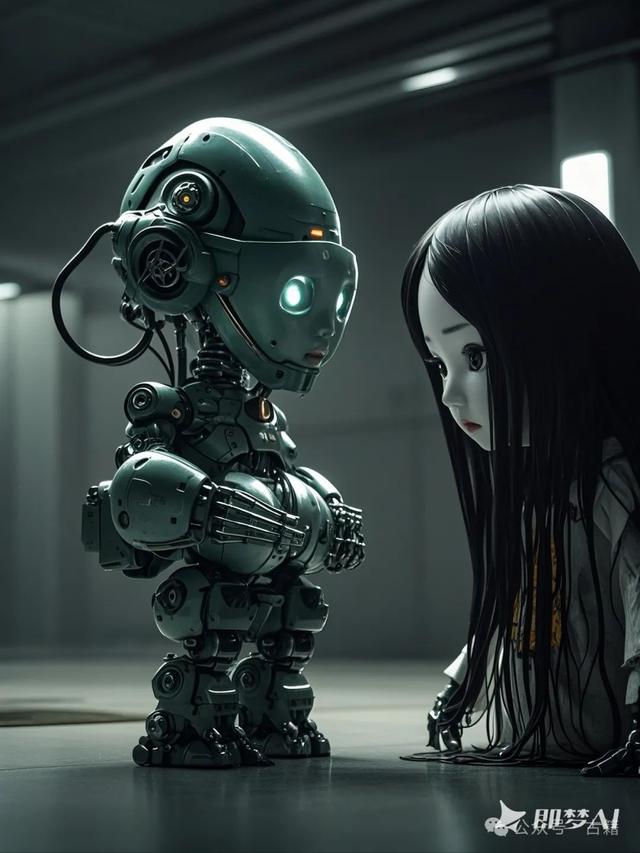
导读:近来人文研究界对于人工智能(文学)写作的讨论已经跃进式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于“产学研”结合的导向,一些研究者选择直接进入对“大模型”(large models)的应用,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直接赋能。在对相关应用的描述中,对“大模型”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大”,即通过庞大的参数量、复杂的联结方式和巨大的训练成本达成的文学创作体量与速度上的爆发。但如果“大”是“模型”的修饰词,那么“模型”本身是什么?人类的认识和创造力中的“模型”与“文学模型”在什么层面上可以触及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在这一视角中,我们将进行另一个向度上的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不能做什么”的讨论。
模型的“祛魅”与“存魅”
在“大模型”之前,提及“模型”的概念会将我们引向几何学。在文学理论的辐射范围内,最早也是最简单的几何模型来自《理想国》的第八章。在这一部分,为了证成善的理型,柏拉图给出了三个譬喻。除了最广为人知的“洞穴喻”之外,柏拉图在“线喻”中通过等比例切割的方式,在一条线段上分出了4个区块,其中两个属于“可见之物”,另两个属于“可思之物”。其中,算术与几何学被归于“可思之物”的较低区块,是介于抽象思考和利用感官事物思考两者间的过渡区。这一区块不以寻找第一原理为目标,而是以演算的结论为终点。[1]虽然和其他的譬喻一样,“线喻”在此被提出的目的也是阐述善的理型是智性成长的终点,但是就这一“模型”本身来说,客观上它呈现了其基本功能,即标识出抽象思维与感官实在之间的间隙或者混合区,而这一区域本身就对应着数学所表征的存在状态:即非完全的抽象,也非感官能直接把握之物。或者用柏拉图自己的分类来说,作为“模型”的几何学的功能,就是使抽象思维中某些不能直接对应经验实在的“物”能够被直观。
在“实在”尚不成为一个问题的时代,古希腊人的数学观完全建立于直观与经验的基础上。虽然古希腊人与古巴比伦人很早就使用除整数之外的分数与无理数,但也仍然以整数为唯一标准,进而取这些不可公度数的近似值,因为整数的经验形态是可以被感官直接把握的。“不可公度”在当代哲学中往往被泛泛地理解为没有一致的还原标准,而在数学中,它实际上的意思是不能以整数表达的比值。尽管如此,古希腊人并没有选择对这类特殊的数熟视无睹。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曾明确表明要探索关于“不可公度”的知识。欧几里得几何学是这种探索的产物,它可以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系统的“模型”。但严格来说,欧式几何并没有真的提供柏拉图所要求的“知识”,而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对整数的逻辑处理使得无理数得到了直观的几何学表达。当1和2都被当作线段时,“不可公度”的问题就消失了。[2]128
在欧式几何占据主导地位的至少1600年时间里,数因此与几何学完全区隔开来,“模型”将“不可见”之物完全隐没了,直到解析几何的出现,它的出现通常被归功于笛卡儿。解析几何也被称为一种“数形结合”而非“数形替代”的方案,这与欧式几何的功能意图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迈克尔·弗里德曼在一篇讨论康德几何学观念的论文中就利用解析几何“显灵”了欧式几何中被隐没的“不可见”之物。在《几何原本》的第一个命题中,在一条已知有限直线AB上做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方法,是以A与B为圆心,以AB为半径做两个圆,以两个圆的交点C分别做AC和BC,得出等边三角形ABC。弗里德曼指出,实际上C点是一个“不存在的点”,因为并没有任何一条定理与公设能够保证点由“相交”产生。并且如果将这个图形放置于直角坐标系中,该点的纵坐标为无理数,故而是“非实存”的,只有依靠近两个世纪后现代逻辑中的“连续律”才能使之实存。[3]不仅是“相交”,欧式几何对比如“相邻”与“线上存在点”也未作定义。从严格的几何学逻辑角度看,过多的“未定义量”此时开始被视为欧式几何的缺陷,因此后续诸多非欧几何学模型所做的“改进”就在于加入“未定义量”需要满足的公理,使得“未定义量”能够得到与已有公理系统不矛盾的阐释,所得到的这个阐释就被作为“模型”保留下来。
尽管上述发生在几何学史中的转变似乎是一种对称的自反,但模型的功能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它始终都是对“未定义量”的阐释,而这些“未定义量”又恰恰是在我们将“不可见者”归于“可见”的逻辑表达时被催生出来的,虽然这些被催生的“不可见者”本是我们在尚未怀疑的实在经验之中默认的“常识”。在后面这个意义上,“未定义量”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对日常的保留,这意味着我们在按照现实世界的“模型”去进行思想活动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虽未被纳入严格抽象的公理系统却确实存在的事物。值得一提的是,解析几何的主要发明者笛卡儿同时也是第一个将外部实在引向怀疑论的人。在通常的表面理解中,这无外乎产生了真实与虚幻的对立,但结合他在几何学上的成就,特别是从将“数形结合”视为非欧几何模型的诱导观念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影响实际上要更加深远。这一后续进程意味着为了消灭“未定义量”,几何学模型不惜付出“扭曲”实在世界的代价。
几何学史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模型史”的这两个阶段虽然在“提纯”逻辑功能的层面是一致的,但如果说非欧几何模型是一种严格的“祛魅”,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对当代感官条件下的“现实世界模型”的“扭曲”,那么欧式几何所做的则相对是一种“存魅”或者“悬魅”。对后者来说,限于整数的逻辑推导划定了一个感知界限,一旦我们要严格履行这种逻辑推导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同时面对“未定义量”的涌现。它们不是外来的,而是就被悬放在我们所建立的面向有限世界的“模型”之中。在这一层面上,柏拉图的“线喻”通过最简单的几何学模型显现了这一“未定义量”的区块,它在朝向“智性成长的终点”的语言表述中会被轻易带过,但在“线段”这一几何模型中显露无遗。对这一区块的正面解释便是:在对“智性成长”的逻辑处理中,我们在某一个区块看到了我们本不应看到的“不可见者”。在对现实世界的“模型阐释”中,非逻辑的“常识”以他异之物的身份被对象化了。
在此我们可以回到文学。当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章决定驱逐诗人和艺术家的时候,这一行动的依据可以被理解为后者会停留在“智性成长”的某一过渡阶段,并通过刻意钻研这一过渡区块中的伪知识而进行文艺创作活动。文学家和艺术家就如同痴迷于欧式几何作图自身的人,只是单纯地进行逻辑建模,而这一行动带来的愉悦不是真理的确定性,而是某种穷尽逻辑推导之后涌现的他异之物。无论对这一活动在追求真理层面上的价值褒贬与否,这确是文学的“模型需求”,或者说是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文学模型”的标准诉求。实际上,除了近几年开始出现的“设定系”推理(在预先设定的非欧空间世界模型中展开的推理文学)之外,文学模型仍主要停留在几何学模型史的前一个阶段。标准文学模型的潜在生成目标,也就是文学在感官实在中涌现的“未定义量”有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具体形态:幽灵或者说“鬼故事”。
“三一律”与“鬼故事”
如果将上述“模型”思维带入文学,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模型”无疑是“三一律”。与中文翻译的字面感受不同,“三一律”(Unities)对应的英文的意思并非主要指多种不同范畴上限制的综合,而是对应“单位”(Unit)这一词根,它直接来自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几何原本》的七至九章,欧几里得对“单位”的定义是指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把诸多存在于事物中的每一个称作“一”,一个数则是由多个单元合成。这个定义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略了“未定义量”的必然出现,而对于整数逻辑推导来说它们又是必要的。[2]126但相对地,这一几何学模型的“缺陷”也就逆转地成为与之同源的“文学模型”的潜在指向。“文学模型”的这一原则并不主要引发真实与虚构间的对立,而是在直观“可见”的框架下对“不可见者”的催生。
正如新媒介研究中经常用“视觉中心主义”一词来标识一种需要被打破的古典标准,“眼见为实”的模型基础所指向的“一”,或者说整数逻辑推导原则在原理层面涵盖并解释了“形式—实在—观念”在柏拉图哲学观中的统一。这正是最简单的“线喻”模型中涌现的原则,并且它直接关涉数、数学与几何学中切实具有的“知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当代模型“数字化”观念的哲学源头。而在最初的文学理论文献也就是《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此所做的改进是,在文艺作品试图以这一“模型”原则对世界进行推导的时候,似乎总要遭遇将问题带回几何学模型的诱惑,即将一切的“未定义量”“无理数(者)”“不可见者”都近似地归入“模型”的“可见”范围。但这种有待处理的一致性也天然地承认了其间的分离,并引发了不可控的张力。它持续地发生在“muthos”这一未经证实的言语与“logos”这一被认为是真实的言语之间,而后者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整数逻辑推论的“阐释模型”。正如西蒙·戈德希尔所指出的,古希腊悲剧的一个潜在主题,就是非神之人对神谕进行准确阐释的无能,并最终寄托于法律对语言本身的仲裁。[4]在此,神的语言或者说神自身正是“文学模型”的催生物,它们是“三一律”被隐没的基础,却又在“模型”的运作中显灵。
以“文学模型”的视角重看文学史,相应的叙事重点也会发生改变。“鬼故事”在这个视野中就不再是为了迎合大众趣味才产生的边缘题材,反而是在“文学模型”这一科学视角下文学史中自然而然出现的事物。由于主题的原因,我们在此不会对这一故事题材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我们更关注的是其中的核心观念何以与“文学模型”的观念保持连贯。在主流的文学史叙事中,我们知道,“三一律”的地位在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中达到了高峰,但同时也出现了对作为“清规戒律”的“三一律”的变通解释与违反实践。比如,卡斯特尔维屈罗非常明确地指明,之所以要对时空进行“整一”的限制,是为了将戏剧所展现的事情限制在“一个人就能看得见的范围”[5]。这一补充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三一律”作为感官模型的一面。
就“文学模型”本身的实践来说,更知名的人物则是《熙德》的作者高乃依。虽然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高乃依违反“三一律”事件有竞争对手及主流文化圈构陷的因素,并且高乃依自己也并未以此为目标,而只是认为完整的行动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实际上,《熙德》的“问题”非常直接地体现在作者在主干事件部分构造了一个极其激烈难解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一记耳光一直攀升到男主人公不得不在决斗中杀掉心爱之人的父亲,并通过额外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些事件的体量不可能被塞进一天的时间之中。这一冲突叙事的编排可以被看作对“三一律”这一“文学模型”的“无情运用”,即采用相当平面化且粗暴的冲突要素进行逻辑推演。虽然从“人类理解”的角度看,这或许并无必要,但就“模型”的逻辑推导本身来说并无问题,且程序十分明确。《熙德》对“三一律”的破坏点实际上在于,它用男主立下战功这一外部因素来解决前一个叙事中的矛盾,并因此使得“文学模型”中的时间容量变得紧张。也就是说,在“模型”运转的终结处,即本该是“鬼神”出没之处,却是另一个“模型”中的要素抚平了前一个“模型”中的“未定义量”。其实,采用今天影视剧批评中的术语,就能够很好地描述《熙德》中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狗血”和“泡沫化”。而从“模型”的角度说,《熙德》对“三一律”的打破是由于另一个外部“模型”的介入在“文学性”即将产生之处使之被重整回可继续推演的逻辑架构之中:用另一个“感官实在”的要素来填充前一个模型中的“未定义量”,把冲突及其和解重新归入绝对的“可见”。可以说,《熙德》是“三一律”被文学“大模型化”的早期例子,在此文学的“大模型化”即“泡沫化”。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熙德》违反“三一律”事件只是一个插曲,但一方面它极具当代性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在其先行与后续的文学史发展中,“文学模型”是如何持续发掘自身固有的“模型”意识。在高乃依的时代之前,莎士比亚在戏剧中熟练地使用鬼魂甚至魔法等“未定义量”要素。在喜剧《威尼斯商人》中,“文学性”的高潮也来自女扮男装以“未定义量”的身份进行仲裁的鲍西娅。《哈姆雷特》则采取了“未定义量”的前置方式。在很多研究中,研究者都提到老国王鬼魂的话是否为真是有疑问的,而哈姆雷特的悲剧则在于它试图通过戏剧来使得“鬼魂的语言”变得“可见”,而最终也只是让其“世界模型”变得更加不可锚定。在高乃依的时代之后,随着科学主义逐渐在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哥特文学或者泛化的关于鬼魂见证的故事开始大量出现。通过“文学模型”的思维,我们仍然能够在“三一律”和“鬼故事”之间建立一个连贯的解释。
实际上稍微思考一下哥特文学的基本形态,就会发现它与古希腊时期的“文学模型”极其一致,并且呈现为一种更为直观的版本。哥特文学的故事发生地大多位于地处僻远的大型建筑内,这个空间设定凸显了感官的核心性并加大了对“视觉中心主义”者的挑战。哥特文学的主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执着于对周边事件践行“理性建模”的主人公不断遭遇“未定义量”的干扰而最终走向疯狂。比如在亨利·詹姆斯的著作《螺丝在拧紧》中,鬼魂所做的事情并非直接可见的暴力,而更多的是对合乎理性的道德行为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可见”的“情动”意义上暴力。在通常的解释中,哥特文学会被解读为“幻想”或者“心理”小说。但如果说该“文学模型”有作用于心理的效果,这一效果也主要来自“感官”与“实在”之间所发生的“阿基里斯与龟”式的追逐关系,这也是“文学模型”依据其基本原则运转而来的产物:我“看到”了我本“无法看到”的东西,这就是哥特文学的“文学性”。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模型”就与自然科学在相关问题上发生了合流,将“鬼故事”更精准地定位于“视觉幽灵”的层面。斯尔詹·斯马伊奇在其专门研究中提到“视觉幽灵”的问题源于沃尔特·司各特对于“鬼故事”之“文学性”的一种要求。他认为此类文学能够达到最优效果的处理方法恰恰在于不要对鬼魂的面目进行过于清晰的描述,他认为奇幻文学一旦进入了读者的“视界”就失去了其效果。因为这种处理观念,肖像画就成为“鬼故事”里常见的装置。见鬼的主人公往往是通过“清晰可见”的死去之人的肖像画才辨认出自己之前见到的确是鬼魂,而鬼魂本身的面目却被视觉模糊处理了,这同时也使得鬼魂确实存在的证据始终处于缺乏未定的状态之中。[6]
这一处理方式非常符合“文学模型”的运作意图,而相应地,这种“文学模型”意图最清晰的显现也就自然带来了自然科学的反击。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科学组织试图从光学等科学视角将“见鬼”事件重新归入“科学模型”的“可见性”。在这一对抗中,奥斯卡·王尔德是其中的知名人士,他曾经对“心理研究协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给予戏谑的嘲弄,表示对后者试图消除鬼魂存在的旨趣评价不高。但是,王尔德对鬼魂存在的态度也并不是出于信仰或者迷信。正如贾拉思·基林在研究中所讨论的重点所示,王尔德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与当时出现的“非欧几何”与“第四维度”的几何学进展直接相关。鬼魂在此被设想为生活在“第四维”的生物,因为当时非欧几何的研究已经展现了超出三维空间也就是超出欧式几何空间的可能性。[7]换句话说,相比于用“科学模型”来同化“文学模型”中的“未定义量”,王尔德这样坚守“文学性”的创作者认同是可能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而它和现实世界及感官实在捆绑在一起的“文学(几何学)模型”并不“兼容”。对于王尔德这样的极端幻想者来说,“未定义量”如果不是现有“模型”的终点,那么它就意味着更大程度上的“未定义量”。[8]
在此,我们就返回到了“文学模型”最初的起点,在起点与终点,它们都潜在地与“几何学模型”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文学模型”的“三一律”不仅是禁止性的规范,它的运作也展现了神话与世俗化之间的持续矛盾,并形成了文学自身的“真理性内容”或者说“文学性”。实际上,在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主义”文论以及更显著的关于“可见/不可见”的现象学视角下的艺术阐释中,“文学性”和“艺术性”也无外乎是一种基于科学平台的“文学(艺术)模型”所涌现之物,是在将“不可见者”压入“可见者”的“模型”之后,随着“模型”的运作以真正“不可见”的姿态被“看到”之物。那么,如果“见鬼”就是“文学模型”的潜在运作目标,我们能在当下的文学技术化时代的作品中见到这样的东西吗?
“大模型”与计算机病毒
在此,我们通过一部也许已经被大多数读者遗忘,或者即使没有遗忘也对内容有所误解的作品进入新时代的“见鬼”讨论:《午夜凶铃》四部曲。[9]由于在著名的影视改编中主要采用了第一部中的“鬼故事”内容,原著作为一部杰出的科幻作品的面目往往不被人所知。在原著真正精彩的第二部与第三部中,山村贞子的“身份”被揭示为一个计算机模拟世界中类似于计算机病毒的东西。为了通过计算机模拟整个世界的生命演化,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启动了耗资庞大的“环”(Ring)计划。基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人类基因工程计划,生命的全部信息得以被还原为能够被计算机所共享的“数字化”信息,而计算机可以以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极高的速度模拟地球生命从无到有的进度。《午夜凶铃》的“鬼故事”部分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模拟世界中的事情。而在第二部与第三部中,由于模拟世界中的龙司在“死”前察觉到自己世界的真相,于是要求现实世界中的监控者将其“带入”现实世界。而观测者通过数字化基因重组的方式,让这一虚拟世界中的“人”在现实中出生,但同时也将模拟世界中的致病基因带到了现实世界。
这个作品令人惊讶的科学幻想在于它展现了一种极端还原论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下,由于整个世界模型中的所有要素都能够被“信息”所“定义”,因此计算机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才被完全打破了。后来被更多研究者所关注的《黑客帝国》的出现,要远晚于《午夜凶铃》四部曲的成书,并且与前者的现实世界已“空无一物”不同,在《午夜凶铃》中,两个世界可以实际地互相影响,甚至可以发生病毒感染。而这一情况的发生原理又恰恰是被身为计算机病毒的“鬼”所直接展现的。在作品中,贞子通过死亡威胁传播录影带(及其文字记录)的真正目的,是使得处于排卵期的女性接收到这些信息并生下自己,而这种无限传播的结果,就是整个世界最终将变成一个只有大量贞子存在的世界,最终丧失物种多样性,导致世界灭亡。这一结果在作品中被非常科学地称为世界的“癌化”。而这一会造成物种多样性丧失的“信息”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进入到现实世界,并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它只是一种在一切生命体间具有“通用性”的基因疾病,而不是“鬼”。
和这部作品一样,当今天的研究者对“大模型”与“自动写作”乐此不疲的时候,在原理上相关并且曾作为一种技术文化现象在计算机界风靡一时的计算机病毒却令人惊讶地被冷落了。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程序的自动复制研究也在不太受关注的层面并行。冯·诺伊曼在1949年首次描述了计算机程序的自我复制,并且和人工智能的相关文学想象一样,在于计算机病毒的正式命名与相关产业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幻想计算机病毒传播后果的科幻文学作品。1984年弗雷德·科恩论文中第一次将可自我复制的程序命名为“计算机病毒”,他也是第一个明确实践和记录这一传播活动的人。计算机病毒的特点就是程序的自我复制,并非只在它被创建的系统中,而是在其他系统中也能做到这一点。并且,虽然往往会被理解为病毒制造者的脱罪之词,但包括科恩在内的绝大多数编写者都认为,计算机病毒是一种被正常运作的用户程序,内嵌在标准程序中伴随运行。也因此,最著名的一类计算机病毒模式也被文学化地称为“特洛伊木马”。
将这些表层特征带回文学文本,《午夜凶铃》充分展现了计算机时代“鬼”的新形态。如果说有什么让龙司发觉自己身处于一个模拟世界之中,这个发现点恰恰在于,在按照“未定义量”在自己的“世界模型”中按照处理神秘事件的方法“驱鬼”失败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世界中“鬼”在传播中的某种单调性。和王尔德的幻想不同,“鬼”的“单调性”或者说完全的“可定义”“可见性”与绝对“可传播性”,让他“看”到了那个在某一可还原性上完全相同的“世界模型”,一个他可以通过这种还原性去往的另一个世界。而整部《午夜凶铃》所描绘的,则是一个“鬼”沦为单调性的“世界模型”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后果。虽然在技术层面更为复杂,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开始以整个“世界”而非单一序列的行动指令为模拟目标后,我们在运用“大模型”时所面对的表层情景仍无外乎如此。将世界中的语义通过不断求导的方式归入确定的线性感知标准,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实现基于这种平均值标准之上的跃迁。[10]而这就像《午夜凶铃》所展现的那样,这种对语言与文学的削平,无外乎是如计算机病毒机制一般所造成的“文学世界”的“癌化”。
其实,当我们直面当下人工智能自动写作的应用场景时,我们所面对的情形就如同《午夜凶铃》里的故事。必须承认的是,人工智能写作可以在速度和数量上大大超出人类创作者,甚至获得了比人类创作者的作品更迅捷和海量的传播度,从形态上看,这种高速增殖就犹如病毒。在此,“病毒”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修辞,而就是一个原理层面的类比。正如时下流行的网络短剧的“上头感”就直接来自永远不会有不符合预期的剧情发展。因为如果这个创作来自“大模型”,那么它的内容走向就是人类对作品预期的平均值。这种“文学平均值”就如同“特洛伊木马”,当你认为自己在启动“文学模型”的时候,你所启动的可能只是高度还原性的文学的“计算机病毒”程序。在这个层面,我们确实“人人都是作家”,就像在“癌化”了的“环”的世界里,如果你存活了下来,说明你正处于“人人都是山村贞子”的到处是“鬼”的单调性世界里。
结语:人工智能会梦到鬼故事吗?
借用菲利普·迪克的著名小说名称,人工智能会梦到(dream of)鬼故事吗?当然,正如我在一篇论文中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这个句子应该被更准确地翻译为:“人工智能想要鬼故事吗?”行文至此,也许从本文中能得到的答案是:不想。但这并非一个最终判定,而是一个判定标准。当“大模型”能够“想要”一个“鬼故事”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有可能实现人类对文学的“需求”。与此同时,当研究者采用“幽灵化”“设定系”“世界建构”等时尚术语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它们并不仅仅是一些后现代性的修辞,正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才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让我们去反思为什么这些术语在当下用于形容我们一些创作与阅读感受时会如此贴切,因为少有玄妙的概念能够完全脱离某种潜在的历史叙事,只是这些叙事尚未被组织。
仅就文学来说,也许当前我们只是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有所偏移。这个偏移也许来源于一种艺术及文学社会学(包括某种狭义的“分析美学”)思路,这类论述在当下的研究界仍然大量出现,即把“文学(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替换为“什么可以算作文学(艺术)?”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尺度几乎是可以无限降低的。实际上,人工智能“大模型”对文学创作的辅助很直观地应该体现在去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维度完全不同的“鬼故事”的世界。比如在新晋的“设定系”推理中,当作者用一套高维世界去支撑自己的“鬼故事”的时候,人工智能也许可以保证世界规则的融贯,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王尔德在他的时代所设想的“文学性”的新世界,一种由完全不同的“模型”组织的新的“文学世界”。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相关前沿理论中,真正重要的基础性理论仍然是诸如“超文本”和基于“指称理论”的“可能世界”问题。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在国内研究界都曾被提及,但大多都在加速的人工智能人文研究的学术生产中昙花一现。
但不管怎样,无论采用什么创作工具,“创作”的第一推动力仍然在于“心中有鬼”的创作者。当我们听到一些专业的科学家提出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的创造力”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比如地心说体系内部的数据充实度的无限提升,而是跨往日心说的那种“创造力”。从这个角度说,在研究界持续讨论了多年以后,在当前的研究论调中,也许我们对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评估太高了,我们寄希望于它能把“创造者”的身份分派给每一个人。同时我们对它的要求又太低了,我们往往忘记了文学作品的第一评价标准是:好看!而这个评价标准根植于我们对文学的“需求”而非“定义”,它要远远高于能够“算作”文学的那个平均值。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篇:译注与诠释[M].徐学庸译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1024.
[2][美]莫里斯·克莱因.数学简史:确定性的消失[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128.
[3]Michael Friedman.Kant’s Theory of Geometry,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94,No.4(Oct.,1985),pp.460-462.
[4][英]西蒙·戈德希尔.阅读希腊悲剧[M].章丹晨,黄政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5-7.
[5]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69.
[6][美]斯尔詹·斯马伊奇.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M].李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24-26.
[7]Jarlath Killeen.Oscar Wilde in the Fourth Dimension:Ghosts, Geometry,and the Victorian Crisis of Meaning.Scott Brewster and Luke Thurston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to the Ghost Story.NY:Routledge,2018:49-55.
[8]在德国文学中也存在着一种类似的与“魔神”有关的“文学模型”,虽然在相关理解中往往被更为哲学化地理解,但从“文学模型”的视角来看,这类文学的“运作”原则主要体现为并不把“神”与“魔”视为外部对立的双方,而是把其所代表的“未定义量”自身视为理性运作的一个内嵌环节。详见王凡柯.“魔神”的三重语境——试论本雅明《评歌德的〈亲和力〉》中的一个核心概念[J].文艺研究,2024(6):30-41.
[9]在最近出现的研究中,吴璟薇非常卓越地论述了《午夜凶铃》中的媒介传播问题,详见吴璟薇.电子媒介、幽灵之声与媒介的后人类境况[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6):22-32.
[10]关于大规模机器学习与早期线性感知机的关系,详见陈超锐.大语言模型的真实与虚拟[J].天府新论,2024(5):58-5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虚拟现实媒介叙事研究”(21&ZD327)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10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