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其关于中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前言《浪子悲歌》发表于《花城》丛刊第6期(1980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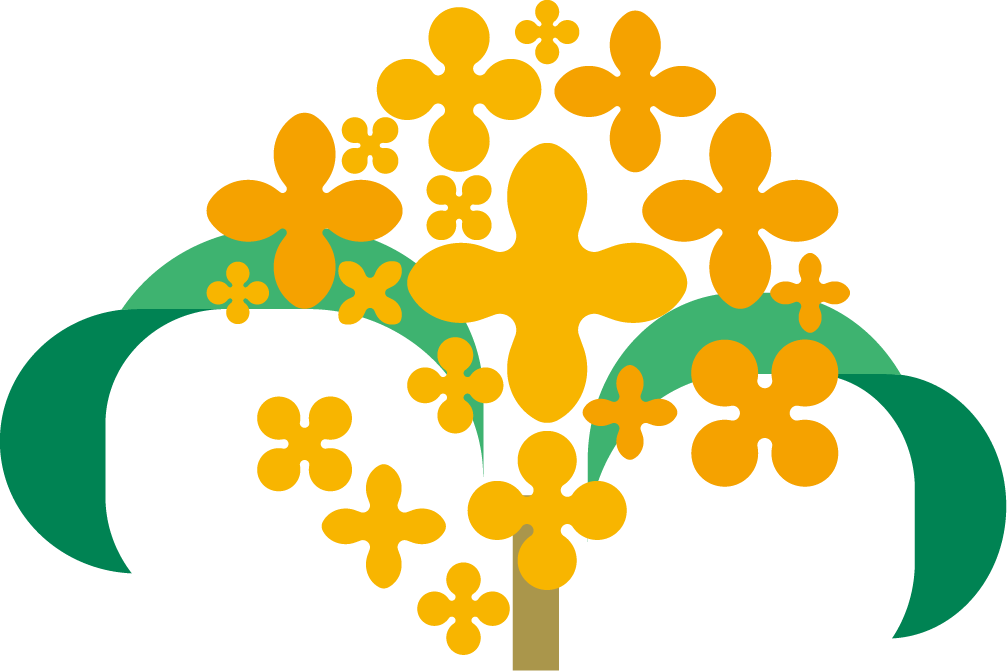
浪子悲歌
——中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前言
聂华苓
我是一个安分的作者。
《桑青与桃红》是一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一个“不安分”的尝试。
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
我不懂那些主义。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什么写法,我就用什么写法。
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真实。《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溶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小说里的事件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只限于它对于人物的影响、以及人物对它的反应。小说中最重要的还是“人”。
我如何在小说中追求客观的“真实”呢?我所尝试的是溶和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戏剧手法、诗的手法和寓言的手法。
我依藉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来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实”,也即是细节的“真实”、事件的“真实”。
我试用戏剧的手法来讲故事。《桑青与桃红》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一九七〇年。我不能把那二十五年的故事全讲出来。当初写那小说的时候,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记满了和小说有关的细节、情节、人物……那些材料可用来写五部小说;但我终于只是选择了桑青一生中四个生活片段,来加以浓缩、集中、深“挖”。那四个生活片断,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在表现主题那个目的上,四个故事又有统一性、连贯性。因此《桑青与桃红》的故事不是由作者平铺直述地讲出来的;而是由作者选好一幕幕场景,让人物一个个登上舞台去表演,作者不加评论,不加分析。作者根本不露面。
我模仿诗的手法来捕捉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借用诗人叶维廉在《中国现代作家论》里评论我的小说时所说的话:“由外象的经营为开始而求突入内象”。我尝试着用诉诸感官的具体“物”象和“意象”,由外向人物内在放射,而照明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不是平面的速写,而是立体的、透明的雕像,让读者去感受,去认识人物;作者用不着用“残酷的”、“恐惧的”、“寂寞的”那一类空泛的形容词去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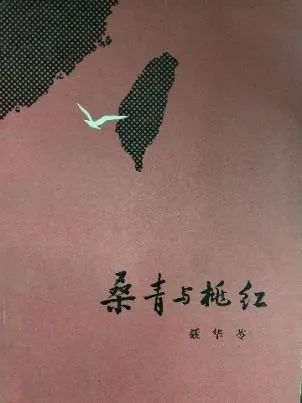
我在《桑青与桃红》中对于语言也作了一个“不安分”的尝试。那小说是写一个经历了中国的动乱又遭流放的中国人精神分裂的悲剧。历史在演进,事件在进展,桑青那个人在变化,小说的语言也得变化——那变化不仅表示桑青由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逐渐变成了一个中年妇人,也得表示桑青精神分裂的过程:不同的精神状态就需要不同的语言来烘托。《桑青与桃红》里的语言从第一部起,张力逐渐加强,到了第三部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的追踪,躲在台北一阁楼里,他们的语言就不可能是一般人正常的语言了。阁楼里的语言是:一字、一句、简单、扼要、张力强,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成为一律的句点了——那是恐惧的语言。
在《桑青与桃红》中,我在形式上也作了—个“不安分”的尝试。小说写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物;小说的形式也是分裂的:桑青的故亊和桃红的故事,双线并行。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
我在《桑青与桃红》的创作中所追求的是两个世界:现实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读者把它当写实小说读也好,把它当寓言小说读也好一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否成功了,但那是我在创作《桑青与桃红》时所作的努力。(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也是那种尝试。)小说第一部“瞿塘峡”所写的是抗战胜利之前“困”(整个小说有许多“困”的意象)在一条陈旧木船上的人,那条木船又“困”在险恶的瞿塘峡,而瞿塘峡一带有许多历史上英雄奇才留下来的古迹,正如小说中老先生所说的:“咱们就困在古迹里呀!”那不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处境吗?老先生象征旧社会;流亡学生象征新生的力量。我很偏爱乡下女人桃花女,她“坐在船板上,抱着孩子喂奶。孩子吸着一个奶,手在另一个奶上拍拍打打,配着吸奶的啧啧声,好象给自己打拍子,又象是要把奶拍出来——一滴一滴,滴在孩子胖嘟嘟的臂膀上。桃花女就让奶那样子滴下去,”我也偏爱木船的船老板,生死关头,面不改色,只是叭叭地抽着空空的旱烟袋;胜利的彩纸在大江上飘飘的时候,他才突然叫了起来山戴帽啦!要下雨啦!船要漂走啦!”船上的人得救了;在浩浩荡荡的大江上流下去了。那岂不就是一页新历史的预告吗?桃花女和船老板是生活在中国泥土上和大江上的人,他们那一股新鲜的原始生命力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维持他们在历史上一场场浩劫中活过来了。小说的第二部所写的是围城(被解放军包围)中旧制度的崩溃;垂死的沈老太太就象征旧制度;真空地带的破庙象征新制度建立之前的荒凉。“一眨眼,风筝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红通通的,在天上照着空空的蔡家庄。”小说的第三部写的是台北“阁楼人”的内心世界;但也是一则寓言故事:台湾那个孤岛也就是一个阁楼。三个不同的人物“困”在阁楼里就有三种不同的心理反应,不同的心理变化和人格变化。人物在不同的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就是这一部小说的“戏”。在这一部小说中,我试用具体的外在真实物象来反射人物内心的“真实”。我甚至于利用了台湾报纸上的广告和新闻报道,譬如:荒山黄金梦;三峰真传固精术;分尸案;故都风物。那都是“阁楼人”家纲收集的剪报,百看不厌。那些剪报反映了台湾社会,是写实的细节;同时也反映了精神死亡的“阁楼人”,对于生命的基本欲望:“故都风物”就是他回归故土的欲望。
小说家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中对于《桑青与桃红》作过如下分析:
……故事开始时桑青是个少女,为了逃避日军而西上,乘着小船在长江峡谷的激流中颠簸,所以故事一开始,就布好了放逐的中国人这意象。第二部以牝平为背景,时为一九四九年,共军兵临城下,在这部分作者创造了沈老太太这令人难忘的资色,她是桑青的家姑,头脑封建,全身瘫痪,奄奄一息,在速乱中不断喃喃地说九龙壁倒坍了;九龙壁是中国皇朝的代表,而沈老太太象征着旧制度垂死的惨痛。小说的第三部题为《台北一阁楼》。这阁楼摇摇欲坠,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顿,不用说,很恰当地象征着台湾本身恐惧孤独、暂与外界隔绝的情况。桑青与夫婿沈家纲躱藏在这阁楱上,因为家纲亏空公款,正遭警方通缉。小说第一、二部分的背景,都是读者所熟悉的,可了解的世界,但这第三部分却把人带进一个脱离现实,象梦幻般的世界,相当于超现实主义画家或荒谬文学作者的境界。小说中提到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在台湾南部有僵尸出没,吃掉了不少人;这情节的含义固然不易以常理推断,不过若有细心挑剔的批评者,认为这个由坟塞复活出来吸生人血的僵尸,其实乃影射旧制度的话,这小说就不免会惹上麻烦了,而事实果然如此。

故事一直发展下去,愈来愈变成了卡夫卡式的梦魇。桑青逃到了美国,但她被移民局追查通缉,象《审判》中的K一样,她与移民局展开了马拉松式的搏斗。当移民局官员问她若被递解出境会去哪儿时,她的回答正具代表性不知道!”这话道破了现代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剧,他们没有地方可去,连祖国也归不得,由牝平流徙到台北再到美国,沿途尽是痛苦与折磨。桑青精神分裂,摇身一变成了桃红,这是精神上的自杀,她的传统价值、伦理现念全粉碎了,道德操守转瞬抛诸九霄之外,沉沦到精神上的最低点,陷入半疯癫状态。到故事结尾时,她还在逃避移民局的缉捕,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顺风车,任由路人带她往别处去……
《桑青与桃红》在国内出版,给了我一个反省的机会。哥德对一位年青诗人谈艺术创作时说:“永远寻求节制。”我在《桑青与桃红》中要表达太多的意义,要作太多的“不安分”的尝试。那小说需要“节制”。因此,我把第四部两个分裂购人格互相斗争的故事删掉了。此外,我想到《桑青与桃红》那样的小说,在国内会有多少读者呢?艺术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不一定相符合。(这儿没有孰高孰低的意思,只是两者求不同而已。)我非常佩服国内的作家那么关心人民;他们为人民而写作。我这个流放的作者到哪儿去找人民?我所能凭借的只有艺术的要求。现在,《桑青与桃红》可以和国内的读者见面了。我自己开始怀疑了:从今以后,我应该为谁而写?我应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艺术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两者之间如何互相适应、互相“节制”、互相提高,而创造出的作品既有艺术性、又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这是我要和国内作家共同探讨的问题,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桑青与桃红》只是一支浪子的悲歌。浪子的悲歌回到老家来唱了——那却是非常美丽、非常动人、非常有意义的一刻。
写于一九八〇年元月爱荷华
文章发表于《花城》丛刊第6期(1980年8月)

聂华苓(Hualing Nieh Engle,生于武汉,湖北应山人,美籍华人,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女性华人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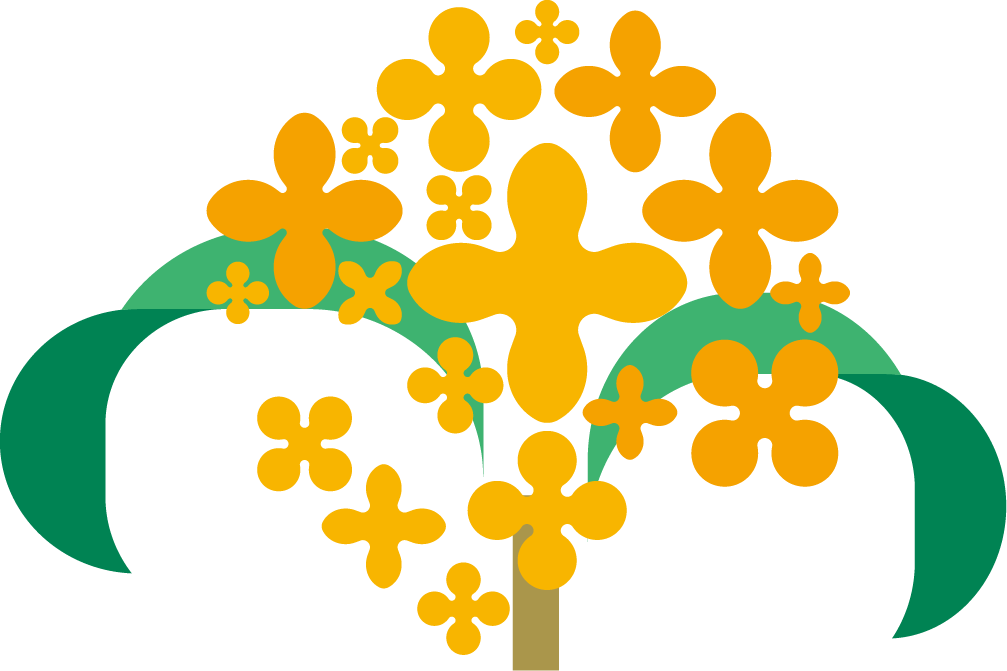


往期内容




2025,年度征订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End
编辑:梁宝星
视觉设计:邢晓涵
审核:杜小烨
点击关注花城杂志新媒体账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