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城》2024年第4期

封面元素:桔梗
设计理念:桔梗独有一份神秘奇异的美,清雅不媚,“花中处士,不慕繁华”。花开时以其灵动柔顺的姿态,在人们的视线中舞动。
导读
天花板是沉睡者的物理苍穹,阳台俯瞰历史的例外,门扉结束了史前人的纯真,广场是世界的华丽封面,阁楼里飞出了诗人的灵魂。建筑是居所,也是迷楼。

建筑的隐喻
赵彦
天花板
一座房子要有一面天花板,是为了控制墙的野心。如果不这样,墙会一直往上长,直到将重心带往摇摇欲坠的危险之地。西班牙语里有一句俗语——“触到天花板”,意思是到头了,碰到了极限。
天花板的存在也有利于我们的目光,它会将我们过于仰望星空的视线弹射回来,弄钝它的箭头,将它折叠进眼皮里,因为再胸怀大志的眼光也需要凝聚,需要内敛,需要回望,需要低头。
天花板还让我们的梦有了场所,再惊怵的噩梦,如果是在天花板下面开始的,都有清醒回来的可能,走得再远的恐惧、浓度再大的悲伤和坠得再深的绝望,都有现实可以折返。我们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天花板那带泥灰的皮肤是让我们平安着陆并且可以喘一口气的地面。

如果说灯重现了宇宙的星辰和日月,天花板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房间里的苍穹,一切都是在我们认识的基础上被布置出来的。在物理上,我们希望一切事物都有边界,我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丈量,大至头顶的宇宙,小至手里那一纳米的灰尘,我们希望被定位,被纳入,被分类,成为地理上的一部分或者生物和矿物学上的一个名词;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必须有某种东西不受其他事物的限制,有一种非个人命运的力量在安排着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它的里边,无起因,也不会结束。存在着这样一种智慧,但我们不知道它叫什么。
天花板在这样一个我们人工建造起来的这个宇宙系统里面:有时候,我们在它下面睡觉,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种“智慧”就是梦,尽管只短到一个晚上,甚至只持续了几分钟。
我们躺下来时世界是颠倒的。因而我们对梦里发生过什么并不那么相信,我们甚至将它视作一个反世界。但每一样事物都需要一个对立面,不是么?
天花板也有它的相对主义。有些天花板在房子里是地板的反面,它是下一楼层的天花板,但却是上一楼层的地面,作为一面平放着的水平的墙,它的功能和名称取决于它位于哪个空间。只有画家埃舍尔能通过空间扭曲的方式将天花板和地面置于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房间内。在他那个矛盾的现实里,上同时也是下,左同时也是右,前面也是后面,里面同时也是外面;每个自己既是自己,也是他人。
每样事物都带着它的反面,就像我们带着自己的阴影降生和死亡。阴影有时候作为我们的补充,有时候则作为冲突与我们终生相伴。在诗人米沃什看来,它更近于冲突,不过并非于我们无益。阴影不只是我们身下那一坨简单的黑色,经常是污秽、疾病、色情、战争、死亡,但它们让我们的轮廓有了层次,有了一个反观和对比的机会。米沃什在他的《路边狗》中说:
这世界层出不穷的复杂和变化多端正是源于世间万物中所蕴含的种种冲突。如果没有屠宰场、医院、墓地和色情影片这些东西作为思想的载体,那么思想的魅力也将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精神和思想居高临下的嘲笑,人类便会受本能欲求驱使,展现出动物性的愚笨。
如果天花板没有下面的地板作衬,一幢房子就会展示出纯粹模仿天空和苍穹的笨拙来。

教堂从来不会浪费它的天花板,它既然被视为一块人工的天空,一座人工天堂,就必须把神圣给补上。就这样,教堂的穹顶作为天堂的宣传栏高悬在我们的头顶。神裸着身子从那里现身,他们钻出湿壁画褪色的颜料,向我们展示运动着的躯体,他们热热闹闹,并不顾及我们在底下维系着的这份用以凝视他们努力做出来的宁静和肃穆。只有在教堂里,天花板才最像天空,不仅因为这里的天花板都被搭建得很高,还因为那些受赞助人委托的画家经常将它们画成天空的模样,给它们镶上饱满的白色云朵,涂上蓝颜色的底色,让小天使们从一云又一朵的祥云间调皮地探出他们永远不会发育的小鸡鸡,彼时,众星辰也已是具体的十二星座了,风则如人间一样毫无顾忌地穿过那些成人神的衣袂——神总是心不在焉地披着那几缕破布,很少衣冠楚楚。在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穹顶,那些衣袂被风刮跑的神形象更加出格,个个都像健身房里刚做完肌肉拉练的运动员,连女神都健壮得青筋暴起——可能是画家是男同性恋的缘故。说真的,我们对天空的想象多少受了希腊神话和各类宗教文化的影响,那儿被描绘得像某个市集上吵吵嚷嚷的广场:男神们手持卷宗和吉祥物不知疲倦地高声辩论,女神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像调情突然被中断,各种版本的耶稣一律头顶光环在一圈使徒和信徒的环绕中一如既往地饶舌,壁画绘画者们急于为传说寻找源头和连续性,因而把过多尘世的东西挪移到了天堂或者天花板上。与头顶那个喧嚣和充满纠纷的世界相比,下面的教堂大厅则安静得更像天界,做礼拜的人和游客永远一脸的凝重,他们把摘下的帽子拿在手里,另一只手则按嘴唇上,这时候从天花板经过的任何一只虫子的窸窣都会被认作天堂的福音,而透过花窗的那几缕昏暗的光从此成为光的种子。
最为著名的教堂天花板当数意大利佛罗伦萨西斯廷教堂的穹顶壁画了,受教廷委托,米开朗琪罗花了四年零五个月(自1508年5月至1512年10月底)在短廊式的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教堂天顶完成了9幅以《创世记》为题材的宗教画——由“上帝创造世界”“人间的堕落”“不应有的牺牲”三部分组成,343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每天,画家爬上高达18米的画架,借助于并不明亮的烛火,在那里仰起头伸长脖子作画,其作画的艰难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如果说西方的教堂天花板习惯于画人物,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寺庙经常出现在天花板上的则是一些花鸟虫鱼和神兽祥云,甚或经文或八卦图形之类的,而人物形象经常是缺席的——宫殿的天花板也一样。偶尔会有一些木雕人像(通常都是半人半神)作为藻井的装饰物出现在房梁的边角部位,但从来不是主角,这符合东方文化和东方人内敛的性格。在道教文化里,天人合一,天即人,人即天,人从来是与万物在一起时才是有价值的;在佛教故事中,万物在时间上也经常是轮回的,人从来就不是主角,充其量只是“人”这个角色在某段时间里寄居在人这样一具身体里。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些交通工具,乘客是那些在去往涅槃之地时需要不停更换交通工具的灵魂——就灵魂这件事上,我们还经常与动物与植物们互通。我们的东方神也不是一些刚愎自用的指挥者和促狭的捉弄者,而只是一些我们能提问的人,他们的回答也经常似是而非,并不给我们明确的答案,而是督促我们沉思。因而在寺庙或宫殿这类神圣和庄严的天花板上,我们并非将天界视作一个与人间相对的可以抬升我们精神境界的空间,而只是地面生活的一个部分,是出于一种愿望人为地让这里集聚起一批美好和有用的事物,是我们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践基地。我们古代建筑师就这样为天花板发明了“藻井”,作为一种科学管用的建筑结构,除了装饰,主要功能就是避免木结构的屋顶着火,为此,一厢情愿的画师们在上面锦上添花地画了很多虚拟之物——云朵、鱼、莲花、水藻、卦象等,它们据说都能克火,而藻井的造型也正像一口向上隆起的“井”,或一把撑开的雨伞(按照形状,有方形、圆形或者八角形,由细密的斗拱承托)。天上就这样有了“井”,就能保证房屋和主人的安全。这比在上面画一个天堂有用得多。
现在我们只将天花板视作一块可以固定吊灯的地方,我们不在那里筑“井”,也不在上面画画。“天堂”往上,这样的信念我们已经丧失;“神”也不会住在那个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可以去的几乎没有光线和没有氧气的地方。如果我们用上玻璃这样过于诚实的建筑材料,“天堂”这样的概念则变得更为致命,因为无论在夜间还是白天,我们都只能看见几只小飞虫因为挨饿而在我们头顶叫嚣着盘旋,信仰越来越成为我们内心的画面,变得更需要知识而不是忠诚,需要执着而不是顺从;曾经炽热地相信上帝的心灵也越来越成为一块会血管堵塞的肉,在我们的胸口,不再为某种纯粹精神雀跃。
......
未完,阅读全文请购买纸刊
责任编辑:李嘉平

赵彦,1974年3月生,1995年开始在《花城》《小说界》《人民文学》《大家》《上海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有多篇小说收录于《“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出版《我们都是二手动物》等。现为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拉美文学博士,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

点击图片
即可购买
《花城》2024年04期


往期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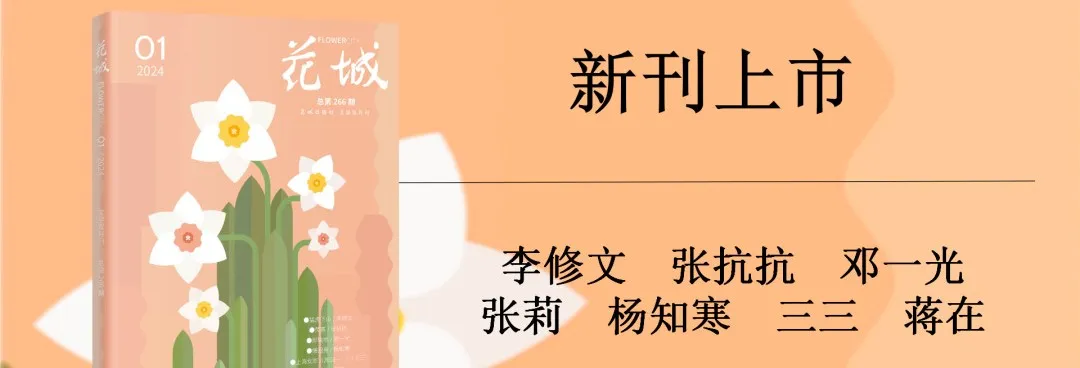



2024,年度征订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End
编辑:王雅喆
视觉设计:邢晓涵
图片:包图网
审核:杜小烨
点击关注花城杂志新媒体账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