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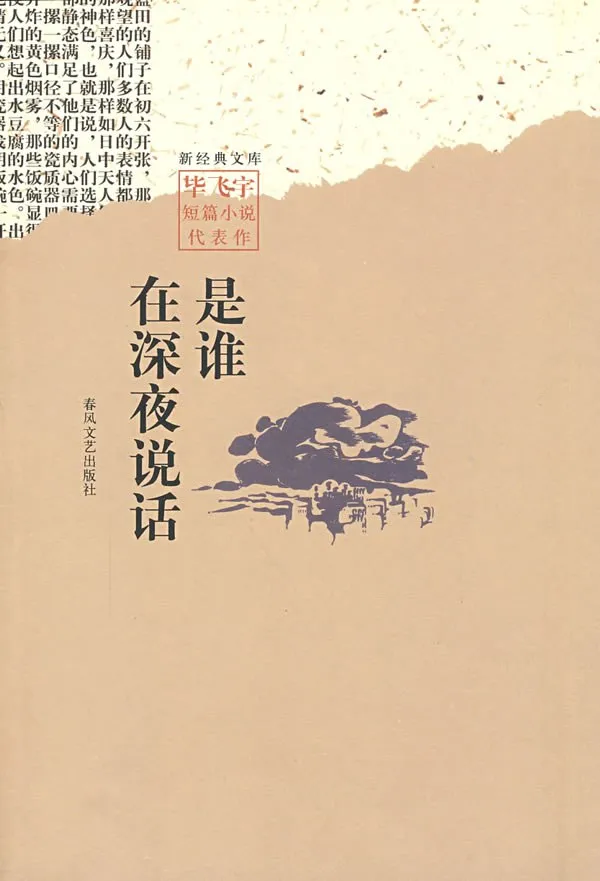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
壹
在具体地谈论毕飞宇的小说之前,想就小说说几句一般性的话。
从理论上讲,小说当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轻率地认定什么是小说什么是非小说。我们难以找到一种小说永久不变的本质。借用一句存在主义哲学的名言,小说恐怕也可以说是“存在先于本质”的。然而,对于每一个小说鉴赏和评价者来说,在理论上认可小说的无限可能性是一回事,在实际鉴赏和评价中,坚持某种对小说的理想则又是另一回事。
就我来说,理想的小说,应该是在世俗与超越之间,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求得某种艺术上的平衡与和谐的。从发生学上说,小说是一种通俗艺术,充盈的世俗描写,鲜活的经验叙述,饱满的形而下层面,本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发展到今天,固然有相当一部分仍只能并且应该作为一种通俗艺术而存在。
但作为通常所说的“纯文学”的小说,则不能停在通俗的水准,它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实现对世俗、经验、形而下的超越,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具有同样充盈、鲜活和饱满的超验层面,有可能并且有必要蕴含着同样充盈、鲜活和饱满的形而上意味。但,小说对世俗、经验、形而下的这种超越,又并不应是以抛弃世俗、经验、形而下为代价的,而应是携带着世俗、经验和形而下的全部充盈、鲜活和饱满,实现对世俗、经验和形而下的超越的。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近十年中,中国小说存在着这样两种倾向:或者一味追求超越、超验和形而上而忽视了世俗、经验和形而下;或者一头扎进世俗、经验和形而下而忘记了超越、超验和形而上。具体地说,八十年代后半期,不少小说具有前一种倾向,以至于使小说显得干瘪、苍白,成为某种哲理演绎;而进入九十年代后,不少小说则具有后一种倾向,以至于使业已作为“纯文学”的小说再向通俗回归。这两种倾向,按我对小说的要求和理想,都是不好的。
而毕飞宇的小说,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便是能对世俗与超越、经验与超验、形而下与形而上进行某种兼顾,便是力求让超越源生于世俗,让超验植根于经验,让形而上蕴含于形而下。读毕飞宇小说,不难看出,作者是一个超越意识很强烈,超验追求很执著,形而上情思很丰富的人。在几乎每一篇作品里,毕飞宇都想要传达某种终极性的迷茫或感悟,某种超验性的困惑或求索。这样一种创作态度,势必使毕飞宇排斥小说的平面化和通俗化。毕飞宇仍然十分钟情于小说的“深度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毕飞宇,其文学性情、文学观念,仍算得上是很传统的。毕飞宇重视超越、超验和形而上,同时也明白,在小说里,超越、超验和形而上必须通过世俗、经验和形而下来传达,因此,在毕飞宇小说中,又可读到较为充盈、鲜活和饱满的世俗描写和经验叙述。
用一句大白话来说,毕飞宇小说仍然是有血有肉的。不过,在毕飞宇那里,超越意识,超验追求,又毕竟对世俗描写和经验叙述形成某种强有力的制约;形而上情思又毕竟对形而下层面实施着某种严格的规范:这便使得毕飞宇的小说一方面重视世俗的描写和经验的叙述,一方面却又不会忘情于世俗描写和经验叙述;一方面要借助于形而下,一方面又不至于沉溺于形而下。
超越意识、超验追求、形而上情思,在毕飞宇那里,使得小说的叙事态度总很冷静。当然,叙事者态度的冷静并不等于叙事者的隐匿,并不意味着毕飞宇小说也属于那种“零度叙事”的范围。在毕飞宇小说中,叙事者一方面是冷静的,另一方面又是处处可见的。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者很少动情,很少对所叙说的人事表示出明确的爱憎,而是常常要流露出某种哲人口吻,常常要摆出一副大彻大悟了的智者面目。
这个叙事者一方面叙述着各种故事,一方面却又显得对世俗和经验意义上的善恶,对形而下层面的是非不感兴趣,他的着眼点在世俗、经验和形而下之上。叙事者之所以以冷静,甚至有些超然的态度叙述着形而下层面的人事,目的也是避免将读者的注意力“误导”到世俗的善恶是非上,而有意识地将读者的目光引向超验的领域,引向形而上的天空。
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者,的确念念不忘把读者引入某种形而上境地。如果说,冷静超然的态度,不对世俗意义上的善恶是非做出评判,还是为了避免“误导”而采取的一种消极手段的话,那么,叙事者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时站出来发几句抽象的议论,则可视作是一种积极的引导了。这样的抽象议论,在毕飞宇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
贰
说毕飞宇小说中也有充盈、鲜活、饱满的经验层面,并不意味着这些经验都是实有的,更不意味着都是作者亲身经历了的。毕飞宇小说中的经验,是一种想象性的。毕飞宇是依靠想象而不是依靠经历写作的。他对小说中的“经验”,持有这样的看法:
“应该说经验是一个相当要害的问题,但至关重要的不是经验,是想象。人只要活着,自然会去经验,只有想象才是经验的本质,或者说,想象是经验的形而上。”(《关于小说的姑妄言之》,载《钟山》1993年第6期)
这说明,他想象的原动力,是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一种终极性的情思,这样,在他小说的“经验”层面中,自然也就会蕴含着超验,而这也同时解释了毕飞宇小说为何不会忘情于“经验”,不会沉溺于形而下了。
超验追求、形而上情思,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不同的指向。而在毕飞宇那里,叩问历史,则是其超验追求,形而上情思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指向。在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身上,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情结”,一种强烈的与过去对话的冲动。因而,在毕飞宇那里,想象,通常便意味着对往昔的探寻,意味着对历史的审视。
我注意到,在毕飞宇小说中,关于历史的议论特别多。前面曾提到,毕飞宇小说中,常出现一些抽象的议论,而这种议论,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历史的。在《叙事》、《楚水》、《孤岛》、《祖宗》、《是谁在深夜说话》一类明显便是在叩问、探寻、审视历史的作品中,出现这种关于历史的抽象议论,让人感到是很自然的。
但另一些作品,如《充满瓷器的时代》、《卖胡琴的乡下人》,仅从故事本身看,似乎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没什么关系。但在这样的作品中,叙事者也会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突然说出一段关于历史的议论。
如《卖胡琴的乡下人》中,有这样的段落:
“知音相遇作为一种尴尬成了历史的必然格局。卖琴人站在这个历史垛口,看见了风起云涌。历史全是石头,历史最常见的表情是石头与石头之间的互补性裂痕。它们被胡琴的声音弄得彼此支离,又彼此绵延,以顽固的冰凉与沉默对待每一位来访者。许多后来者习惯在废墟中找到两块断石,耐心地对接好,手一松石头又被那条缝隙推开了。历史可不在乎后人遗憾什么。它要断就断。”
而在《充满瓷器的时代》里,则有这样一些议论:
“最初满足修史者好奇心的往往被修史者称为历史”;
“矛盾百出造就了历史的瑰丽,更给定了无限补充的可能”;
“补叙历史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别馈赠”。
乍一看,这种关于历史的颇抽象颇宏观的议论,似乎与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本身是相脱离的,《卖胡琴的乡下人》与《充满瓷器的时代》所叙述的故事,似乎支撑不起那种抽象宏观的关于历史的议论,粗心的读者,甚至觉得这种议论出现在这类作品里,有些张冠李戴。但细想想,这种议论,或许正可视作是作者为读者理解作品而设置的路标。有了这样一种议论,人们便有理由认为,《卖胡琴的乡下人》与《充满瓷器的时代》这类作品,仍然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寓言。
在这类作品里,毕飞宇以对凡人小事的叙述,传达着他对历史的感悟、体验、理解。其实,毕飞宇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作是关于历史的寓言。《卖胡琴的乡下人》和《充满瓷器的时代》是这样,《五月九日或十日》、《祖宗》、《叙事》、《楚水》、《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作品,也都可作如是观。
当然,最具有寓言色彩的,还是中篇小说《孤岛》。《孤岛》完全是寓言化的。围绕一处孤岛上的权力斗争,作者尽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历史的感受、见解。我其实挺喜欢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由于干脆采取了一种纯寓言的方式,人们便可自然地把孤岛的历史视作人类历史的某种缩影,而作品中时时出现的关于历史的议论,由于与具体的情境十分吻合,也让人感到自然、贴切、精彩。
而相形之下,《卖胡琴的乡下人》、《充满瓷器的时代》、甚至《五月九日或十日》这样的作品,要从其具体叙述中引出对历史的理解,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如果小说中不设置一些把读者引向历史的路标,我想,读者一般是不会把目光投向历史的。
叁
仅仅指出毕飞宇的超验意识、形而上情思常常指向历史,当然还不够。还须指出,他以小说的方式,到底表达了对历史怎样的一种感悟与理解。简略地说,毕飞宇小说中反复传达的,是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历史其实是不可知的;历史中充满了偶然;历史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历史中到处都是后人根本无法弄清的谜。
对历史的这样一种体悟,自然涉及对时间的认识。对历史与时间之间关系的探寻,也是毕飞宇所倾心的。历史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如河床,而历史则如水流。时间规范着历史的形态。线性的时间,使历史上的种种事件有了先后发生的顺序,而这种先后的顺序,在人们的意识里,便具有了因果性。杂乱无序的历史事件之间,原来也许并无什么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不过是时间赋予的。毕飞宇的《五月九日或十日》,某种意义上,可视作是一则关于时间的寓言(因而,才也可视作是一则关于历史的寓言)。当然,对历史的那种偶然性、无序性、不可知性以及历史与时间的关系表达得最清楚的,还是《孤岛》中的一段话:
拯救扬子岛人的命运与扬子岛人自身的命运之关系,颇似于历史之于时间的关系。不论历史往哪个方向延伸,时间总是不慌不忙地按照自身的速度往前行走。时间蕴含着历史,而历史时常错误地以为自己操纵着时间的走向,说到底,时间的人化才成了历史,换言之,历史只不过是时间的一种人格化体现。宇宙中,真正的、合理的生命其不可逆的一维形式只有一个:时间。时间,作为空间的互逆表现,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与绝对的真……
由于历史中充满了偶然,“只要哪儿出了点问题可能就完全走样儿”,由于历史本无所谓必然,因此,历史中充满了不可解之谜,或者说,历史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谜,而任何试图依据某种逻辑某种规律去复原历史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在《叙事》、《楚水》等作品中,都含有这种意蕴。在这方面,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也值得特意提及。这也是作者将他对历史的感受、理解传达得最富有意味的作品之一。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选择了始于明代的南京古城墙作为其对历史的感受理解的载体,显得颇具匠心。城墙是有足够的资格负载和支撑历史的。作品交叉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居住在城墙根的“我”,“怀念明代”,常深夜在城墙下散步,想像着自己走进了明代,“我行走在夜里,我知道黑夜是没有朝代的,所以我可以在明代散步”。“我”更在楼口的美人小云身上,看到了明代秦淮名妓的风韵。
然而,当“我”终于有机会和小云“苟且”一番后,终于发现,人们其实是不可能重温历史的。另一条线索,是建筑队对明代城墙的修复。建筑队宣称要把城墙修复得如明代一样,甚至比明代“还完整”。当不惜拆迁房屋而收集了散失的城砖把城墙修复得像原先一样,甚至“比过去还要好”后,“我”却发现原先堆放在一处的旧城砖仍然在那里,并未动用。于是,作品以这样的疑问和议论结束:
……我突然想起来了,为了修城,我们的房子都拆了,现在城墙复好如初,砖头们排列得合榫合缝,逻辑严密,甚至比明代还要完整,砖头怎么反而多出来了?这个发现吓了我一大跳。从理论上说,历史恢复了原样怎么也不该有盈余的。历史的遗留盈余固然让历史的完整变得巍峨阔大,气象森严,但细一想总免不了可疑与可怕,仿佛手臂砍过之后又伸出一只手,眼睛瞎了之后另外睁开来一双眼睛。我望着这些历史遗留的砖头,它们在目光下像一群狐狸,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城墙的修复自然隐喻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修复。而历史其实是不可修复的。一切对历史的修复,都不过是当代人对历史的主观解释,都离历史真相相去甚远。而且,对历史修复得愈是“合榫合缝,逻辑严密”,便离历史真相愈远。残余的城砖,意味着历史永远有着“神秘的余数”,意味着人们永远不可能把任何一段历史观察得明明白白,解释得清清楚楚。
《是谁在深夜说话》,由于对历史的感受理解与作品所叙述的具体情境有天衣无缝的吻合,所以让人感到自然、妥帖,即便那种关于历史的抽象议论,也像是从城墙上长出的草,丝毫不让人感到突兀。
肆
在毕飞宇那里,所谓“历史”,常常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他常常是面对整个人类历史而叩问、探寻的。然而,作为特定民族的一员,任何热衷于与历史对话者,都免不了要具体地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毕飞宇也不例外。在一部分作品中,毕飞宇具体地传达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感受理解。而且,毕飞宇还并未止于此。在另一部分作品中,他还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家族史的兴趣,还着力于写出家庭对个体生命的各种方式的塑造、制约。
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毕飞宇有这样一种观察:最美好的与最丑陋的,最圣洁的与最猥亵的,最崇高的与最卑下的,最干净的与最肮脏的,往往离得最近,甚至合而为一。这样一种认识,在中篇小说《楚水》里,有很耐人寻味的形象化表现。在楚水县城被日本军队占领后,冯节中(这名字取自屈原诗“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以这样的诗意命名的,却是一个极为卑鄙无耻的人)这个“在北平读过大学”的人,却从刚遭过水灾的家乡骗来一群姐妹,开了一座妓院。他以“沁园春”、“念奴娇”、“摸鱼儿”、“满江红”这些词牌为妓女们命名。小说特意在被称作“满江红”的妓女身上多写了几笔。有一次,
“冯节中望着满江红很突然地想起了另一样东西,不可告人,是一首他最熟悉的词。这个念头使冯节中的后背上惊出了些许冷汗”。
冯节中想到的,当然是岳飞的那首气吞山河的“满江红”。“满江红”,既可以是一首抗击侵略者的豪迈战歌,也可以是一个供侵略者享乐的妓女!冯节中望着妓女“满江红”而想到岳飞的“满江红”,并“惊出了些许冷汗”,说明他当初用这些词牌名为妓女命名时是并无“反其意而用之”的用心的,是按照中国的青楼传统而自然这样做的。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楚水》中,被称作“满江红”的妓女,是最具有做“婊子”的“天才”的,她“依靠自己的天才努力成了青玉馆的头牌名妓”。头牌名妓“满江红”与岳飞的“满江红”的同名,是一种巧合,而这样一种巧合,也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特性。在《楚水》中,冯节中一次醉酒后还把皇宫与妓院做了对比,认为皇宫也不过是一处妓院,“一大院子的婊子,就皇帝老儿一根嫖客”。皇宫与妓院,这在社会等级上离得最远的,却又在精神实质上离得最近。
《楚水》中,还不止一次地写到,在妓院中冯节中的屋里,挂满了名贵的字画。名贵的字画成了下等妓院的一种装点。《楚水》对城中“古琴手程老先生”一类“德高望重的遗老”的刻画,也富有深长的意味。这类“遗老”,集最精致的传统文化与最卑俗的灵魂于一身,以最高雅的方式干着最恶浊的勾当: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造就过这样一类人。
而在《祖宗》、《叙事》、《雨天的棉花糖》、《大热天》一类作品中,毕飞宇则表现了对个体的家族史的兴趣,探寻了家族、血缘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在这方面,中篇小说《叙事》值得特别注意。《叙事》把对家族与种族的双重探讨交织在一起,强调了种族认同对个体生命的重要。种族认同也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归属。对个体生命来说,这种文化归属是至关重要的:
“种族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正如文化是生命的本质属性。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灾难。”
在一个人的家族史上,父辈是与自己离得最近的,因而也是对自己最具有影响的。而父子之间,常常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在中篇小说《大热天》中,就表现了两代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尽管在家族史的名义下谈论这篇小说多少有些牵强。
如果说《叙事》中,写到了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灾难,那么,在《雨天的棉花糖》中,则写的是个体生命的特有禀性与文化的错位,或者说,是个体的性情与社会角色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同样是人无法承受的悲剧。我们的文化,为男女两性规定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男人应该有男人的气魄,男人应该有男人的事业。
而《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虽是男子,但却很女性化,他没有男子应有的男子气概,没有男人的豪情与雄心,他从小就是一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
“红豆曾为此苦闷。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
具有这样一种禀性的男子,是注定担当不起他所必须担当的社会角色的(值得指出的是,小说并没有把红豆写成心理变态者,这非常重要。红豆或许仅仅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可算是变态,而在生理和心理的意义上都不是)。然而命运却又偏偏让他扮演最为男性的角色让他走进军营,让他走上战场,让他置身于一种即使是最男性的人也难以忍受的境遇。红豆当然扮演不好这样的角色。他惨败而归。于是,人们对他感到了失望。
小说着重写到了红豆与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红豆是一个太不男性的男人,而红豆的父亲则是一个过于男性的男人。这个父亲是把一条胳膊丢在了战场的英雄。社会(文化)对红豆的期待和强制,具体是通过他的父亲来实现的。由于红豆无法成功地扮演他所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于是,他便有强烈的自卑,有了一种深深的自憎。他渴望脱胎换骨,渴望一次新生。对自己的憎恶和对新生的渴求,终于使他精神分裂,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死去。一个先天禀性与社会角色如此错位的男人,是难以活得更久的。
《雨天的棉花糖》,在毕飞宇小说中,是最富有真情实感者之一,因此,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伍
毕飞宇这一代小说作家,大概没有人能完全不重视小说本身的问题。对小说的技巧层面——从叙事语言、叙事节奏到叙事结构——毕飞宇也是倾注心力极多的。在这方面,最见其匠心的,是中篇小说《叙事》。在这部作品中,毕飞宇刻意追求一种叙事的层次感,多条线索、多种层面,交叉重叠,却又有条不紊。如果单从技巧的角度看,这部作品是很成功的。但读完《叙事》,我赞叹技巧的同时,也感到一种缺憾,即作品内在的意蕴、情感,还没有丰富充沛到足以支撑起这样一种叙事结构的程度。作品缺乏沉实感。因此,《叙事》多多少少地让人感到有点把玩叙事,卖弄技巧的味道。
毕飞宇的“历史情结”在以后的作品中如何表现,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毕飞宇对历史的一些基本感悟、理解,在已有的作品中已重复表现过。在今后的作品中,是否还应该这样重复下去?固然,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终生都在重复地写着同一个问题。但这可让以毕生心力与之纠缠的问题本身,一定是内涵很丰富的,而且这问题,也必定是与作家个体的生命存在紧密相关的,作家不仅仅是在抽象地思考这一问题,而且也以自身的生命存在体验着这一问题,不仅仅用大脑而且用心灵与这一问题对话。
而毕飞宇的“历史情结”,比较起来,内涵还显得抽象、单薄了些。要继续与历史对话,历史眼光也许还应该更细密些,历史视野也许还应该更开阔些,要写出在现实生活中具体感受到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是写之不尽的。
毕飞宇是属于那种内敛型的作家,沉湎于内心,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依靠想象而不依靠经历写作。这种类型的作家,通常与现实、与时代,保持着一段距离。保持一段距离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但保持距离却并不等于漠不关心。任何一个好的作家,都应该与时代与现实,确立一种合理的关系,都应该找到一处审视时代和现实的精神立足点,都应该是为时代和现实的一些最本质的问题而动心的。
毕飞宇热衷于与历史对话,但我想,绕开自己置身的时代,越过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现实,是很难真正从历史那里听到什么有价值有意味的东西的。不屑于与时代与现实对话的人,历史恐怕也会不屑于与他对话的——当这个人是一个小说家的时候,情形恐怕就更是如此。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写完了,还未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正寻思间,想到了作者的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想到了那个住在城墙根下,常在夜间游走于墙脚,幻想着走进历史的“我”。而我知道,目前的毕飞宇,也的确是栖居在南京的古城墙脚下一间租来的平房里,阴暗而且潮湿。在这个意义上,《是谁在深夜说话》中的“我”,正可视作作者自身。于是,我想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城墙下的夜游者》,我觉得,这是大体合适的。■
(本文为作者为毕飞宇小说集《祖宗》所作的跋语,转载自《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媒体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