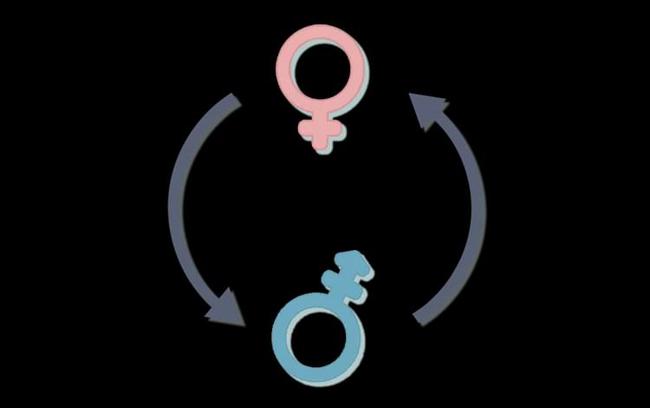
作者:卡琳·阿格斯坦(Karin Aggestam),隆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教授兼中东高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和平外交、性别、冲突分析、谈判/调节和中东区域研究。安·唐斯(Ann Towns),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外交与性别、性别和文化多样性、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等。
摘要:本文认为,外交的重构与性别以及长期以来排斥和接纳女性和男性的做法密切相关。尽管学术界之间的大型辩论都涉及到了过去一百年来外交的变化和连续性,但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微乎其微。因此,本文的首要目标是推进一项新的研究议程,激发未来的性别研究并对外交产生积极的反思。新议程提出了三个不同领域的外交学术叙述,主要集中于:外交历史、描述性代表和性别机构。本文的结论是,首先需要将视线从欧洲和北美移开,更加关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第二,有必要超越描述性的个案研究,转向更系统的比较,以追踪由来已久的性别动态(gendered dynamics)。民族志(Ethnographic approach)[1]的工作可以为性别微观过程和日常的实践提供新颖的见解。第三,作为外交领域性别转变的一部分,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可以为外交变革带来重要的理论贡献。
要词:外交;性别;谈判;实践;女性;和平与安全
文源:Karin Aggestam and Ann Towns,“The gender turn in diplomacy: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06 Jul 2018,pp.9-28.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39期,总第39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审校:杨朔,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朱翊民,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精选
一、引言
外交在传统上和形式上都是男性的专属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家和国际组织逐渐开始让女性担任各种外交职务,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男性依旧在外交中占据着较多的席位。外交领域逐渐向女性开放的过程伴随着国际女权运动争取性别平等的广泛动员。20世纪90年代,在充满活力的跨国联盟、国家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更广泛地参与了外交事务和许多其他的国际论坛和领域。联合国安理会于2000年通过了关于妇女、和平和安全(Women, Peace and Security)的第1325号决议,将性别平等作为更广泛的和平和安全关切的一部分,该决议是妇女争取参与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近些年来,也有一些推进将跨性别者纳入某些外国服务机构的努力,例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积极推动跨性别外交官和其他的性少数群体(LGBT)[2]成员的加入。
但尽管如此,性别和外交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依旧滞后,这一领域尚且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外交性别动态的疑问。本文的总体目标有三个方面:(1)对正在进行性别与外交学术研究进行评估;(2)确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3)提出新的性别与外交研究议程。
二、适时改变——过渡时期的外交
像所有的其他概念一样,外交这一概念也是有争议的,存在着多种解释;因此,可以说外交是“一种内在的多元事务”。至今,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已经被视为是被授权代表某个国家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个人。现在的性别研究已经助力于发掘和突出女性在未获得正式授权情况下所发挥的关键支撑作用,女权主义者努力拓宽、改变和重新思考对外交的理解。作为出发点,我们将外交视为一套以和平方式管理国际关系的假设、制度和程序。
外交往往被描绘成一种由一群具有训练有素的敏锐直觉的男性外交官来进行实践的、基于传统和历史先例的艺术。这一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外交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连续性和变化的特征——已经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辩论。我们正在见证一种与“旧”外交(双边、私密、精英/专业化)不同的“新”形式外交(跨国、多边、公共、多元、政治/民主)吗?为适应不断变化且具有挑战性的全球化和跨国治理,外交在多大程度上调整了其规范?外交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来理解这些重大且复杂的转变,例如公共外交、跨社会外交等被广泛运用以评估新的外交过程和实践。另一种说法是官方外交和非官方外交的区别正在消失,随着国家主权领域的拓展,外交更多地专注于跨国问题而不是国家。
然而核心辩论几乎没有将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也没有把女权主义理论纳入解读当代外交实践变化的一部分。虽然事实是近代历史中男性垄断了外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参与外交事务数量有了大幅上升,但公开的非二元性别者和跨性别者参与正式外交的情况仍然少见,在大多数的实证案例分析中也没有出现性别敏感部分。我们需要探索和拓宽分析范围,研究各个外交轨道——通常指官方外交、非官方/非正式外交——之间的互动。
但过去20年,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外交和谈判,性别研究领域也有了一些进展。本文建构出性别和外交研究的三个扩展分支,它们构成了该领域的性别转向:外交历史、描述性代表和性别机构。
三、外交历史
外交史研究主要考察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在欧洲外交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但不幸的是,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妇女参与社会外交活动的研究依旧很少。
通过追溯妇女参与欧洲外交的历史根源,外交史学者已经明确表示,妇女参与外交活动不是一个新现象,妇女投入外交的历史可追溯到比她们20世纪担任外交官和外交官夫人角色还早几个世纪。在禁止妇女担任正式国家职务的欧洲禁令出现之前,早于19世纪时妇女偶尔会担任外交谈判代表,甚至可以被任命为驻欧洲大使。
虽然妇女偶尔担任正式外交职务,但她们的非正式参与更为广泛。19世纪和20世纪时,随着外交重心逐渐转向专业化和官僚化的外交部(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女性这一性别类别被明确和正式地禁止担任外交职位。这一举措的主要影响表现在非正式的外交官夫人制度上。外交官的正式角色是为男性所预留的,且更为偏好异性恋男性精英,外交官的妻子则充当着外交互动的推动者。她们曾经做过——现在还在继续担任——招待会和晚宴的女主人、民间团体联系的志愿者和丈夫的参谋。
也有一些关于20世纪女性争取担任正式外交职务和外交职业的研究,但也仅限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区域的研究。为了建立对何时何地正式外交场合首先对女性开放的完整认知,对非欧洲地区的外交部研究是必要的。现有研究细节丰富且背景复杂,但都聚焦于独立的外交部研究,因此没有很多对于女性参与外交的国际趋势和模式的探讨。解除对女性从事外交活动的普遍禁令是有外交生涯追求的女性工作的一个关键步骤,但这障碍重重。在许多案例中,国家禁止已婚妇女担任外交官,只有单身女性才被允许参加外事服务考试。结婚和外交事业,女性只能二选一。
总而言之,现有的研究成果明确表明,欧洲妇女在19世纪之前确实担任过正式的外交官和大使,尽管这样的任命并不常见,但确实发生过。更多的情况是女性作为王室成员,依赖于她们作为妻子、情人、朋友、母亲、姐妹或者女儿的角色来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影响外交。虽然她们本身不是国家官员,但可以接触到当权者的精英女性有着多种方式可以参与外交,比如提供建议、收集和传递信息或传播虚假信息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交转向专业化和官僚化时,女性被禁止担任官方外交职务,“外交官妻子”逐渐制度化,这种无偿和不被承认的付出对正式运行的外交有着重要作用。最后,从研究中我们得知自禁令后女性一直在为取消外交禁令和婚姻禁令、承认和规范化外交官妻子的工作而作斗争。
在性别和外交史领域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善。其一,现有研究往往采取案例分析,分析的时间、空间都相当有限;其次,外交领域很少有关于性别和跨性别的学术研究;再次,需要对非欧洲外交史进行更多的研究。随着对历史的不断发掘,我们可以对女性、男性、跨性别者或非二元性人士如何以及为何参与或被排斥在外交活动之外做出更丰富的理论解释。
四、代表权和对包容性的追求
男性一直以来都在外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参与外交的妇女人数也在增加,外交的性别构成正在发生着变化。现存的少数研究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并证实了大多数顶级外交官都是男性。唐斯(Towns))和尼克拉森(Niklasson)在一章研究中表明在职业外交官的最高职位——全球大使的任命中女性占比15%,这些大使中无一是公开的非二元性别,在高级谈判职位中女性的数量更少。因此,执行核心谈判活动的主要都是男性,而女性则倾向于以观察员和公共顾问的身份参与,或者仅纯粹参与行政工作和担任支持性角色。此外,男性在国际组织内的过度代表也有着类似的模式,这反映出了外交的性别结构。例如,同样是在欧洲理事会,很少有女性被任命到更高级别的委员会和外交政策领域,女性在最高部长级别职位上的比例是所有欧盟机构中最低的。仍然有必要对世界上现有的大多数外交专业代表以及国际组织和谈判论坛中从事外交工作的男性、女性、非二元性别者以及性别流动人员的数量进行基础的经验测绘(empirical mapping)。
许多主张在外交活动中增加妇女代表的人,重视女性在促进外交效率方面的能力。这点在当代政策话语中表现明显,这些话语倾向于将女性同性别混为一谈,并建立在女性天生和平的本质假设之上。然而,我们需要探讨外交机构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容纳女性可能带来的或需要的差异性?尽管有更多女性加入外交领域,外交实践和具体产出是否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去几年学者们做了一些有趣的研究,用以评估和平谈判和协议中代表和产出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贝拉(Bell)发现,联合国SCR1325启动以来,将性别条款纳入和平谈判和协议的趋势愈发明显。根据斯通(Stone)的研究,妇女的参与将使和平协议在一段时间内生效的几率提升20%至35%。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对将外交领域描述性代表转向实质性代表进行更多研究。
五、外交的基础设施——一个性别机构
在性别与外交研究中,机构的概念一般有两种核心含义:一是作为具有明确目标和规则的正式组织,规定有权力和责任的指挥链与机构职位;二是作为不那么正式但却持久的一系列关系、实践和行为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的研究中,机构本身被视为性别的支撑者,而不仅仅是涉及担任外交官的人。女权制度研究表明,制度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可以是性别化的。就其本身而言,制度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这些规则和惯例根据角色和情况之间的关系来定义适当的行动”。由此建构的性别将有助于把个人的期望和做法塑造成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模式。
男性化的权力规范在和平谈判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因为这与安全利益和军事事务密切相关。在最近的一个对50多位调停者进行的访谈调查中,阿格斯坦(Aggestam)分析了性别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和平谈判的进程动态中运作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在谈判过程中妇女、和平和安全问题是如何被“隔离”的,只有女性谈判代表才关心,而关于大男子主义的讨论则全然不在谈判之中。
先前的研究也表明,外交部——更正式意义上的机构——可以有成效地被认为是性别平等的机构,这些机构似乎有可预测的劳动分工,包括熟悉的男女性在责任和任务之间的分工,女性往往最终支撑“软”政策领域而男性往往集中在“硬”政策领域并在领导层获得了多数机会。女性进入外交领域时似乎就有了这种分工,例如,诺伊曼(Neumann)描述挪威女性在进入外交领域是首先就是打字员职位,然后是具有“温和”职责的公务员岗位。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务院也是这种模式,公务员主要由女性出任,而外交部主要是男性出任。
一旦越来越多的女性被招募进国际谈判或外交服务职业渠道,这些在等级和劳动分工方面的差别就可能会减少。但是制度特征也是妇女担任低级别领导和其他高级外交职务的核心关注,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的领域。首先,处于中心地位的男性网络可能会影响招聘和职业发展——可能资深的男性会更倾向于注意、鼓励并让男性作为新同事参与进来,这使得男性后辈比女性后辈更容易受到支持和鼓励,从而激励了他们采取措施推进职业发展。再次,还需要对向女性公开地或隐晦地表明她们不适合从事外交活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这种暗示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担心女性无法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有效建立关系网;担心女性不能将高标准的外交职业同婚姻和生育相结合;不愿将女性置于暴力环境中;认为女性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保守机密。性骚扰常常不成比例地发生在女性和跨性别者身上,所带来带来的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使得他们对外交事业投入减少,甚至完全放弃。此外,外交活动一般没有妥善的安排能够使家庭生活和工作相结合,这对女性尤其有害,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担着更多的照顾责任。强有力的产假政策、提供育儿服务以及父亲对照顾孩子的更多参与都是必要的,然而,除非外交领域的职业期望能够发生变化,否则女性接受休假政策反而会影响其职业发展。
六、结论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具体的实践者之中,争论的焦点都始终聚焦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延续性上,性别问题却鲜有人关注。因此,通过对现有性别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并提出了在外交研究中进一步推进性别研究的多种途径。作为结论,我们列出了一些我们认为特别适合的研究领域。
首先,这一领域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我们需要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更多研究。其次,需要超越描述性的单个案例研究,转向更系统的比较和更大的“N研究”(n-studies)[3]。还需要对性别的微观过程进行更多的民族志研究,包括在外交机构中工作的性别规范、关系和身份认同。民族志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揭示低级别的阻力以及促进制度新发展的零碎变化。最后,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可以为分析性别、权力和外交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概念框架和实证指导,协助探索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推进变革性和包容性的外交。
译者评述
本篇文章于2018年线上刊登在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杂志上,文中两位女性学者试图在外交领域学术研究中引进新的研究议程,指出了性别和外交方面学术研究的滞后性。
当人们谈论性别议题,最先在脑中浮现出来的应该就是“性别平等”这个词,一直以来女性为了争取自身权益实现平等在各个领域不断展开斗争。事实上,国际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至今不过也才二百余年的历史。欧美女权运动史上第一次浪潮便从解放妇女参政议政开始,其中,在英国直到1908年男女平等选举权的提案才获得通过;在美国1919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4]。可以说女权运动率先在政治领域开始,但相对集中在国内政治领域。现今语境下貌似人们对如就业、婚姻自由等社会领域女性权益的关注度更高,而本文聚焦于外交领域,具体举例中揭示了女性在外交领域面临的困境,包括任职机会的不平等、婚姻生育和工作的抉择、在外交机构中具体工作分配暗含的性别偏见等等,与其他领域女性面临的困境竟是如此相似。只是人们缺少对外交领域内性别议题的关注,但这些问题真实存在。
本文通过主要参考来自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外交史料和实践,在这些地区外交领域长期以来似乎是男性专属的领域,能够有接触外交环境的女性本就寥寥无几,具体的例子中女性都是处于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发挥着外交作用,女性的自主意识和能力在其间几乎都被忽视。“结婚”和“外交事业”的二选一难题几乎从来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比起男性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生育和照料责任,对女性就业造成不公,这也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种体现,损害了外交女性的权益。
除了女性在外交领域面临的困境之外,作者在本文中也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性少数群体的外交权益缺乏关注。但本篇文章整体论述较为简单,更像是抛出一种思想,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两位作者在结论部分理性地指出了其研究的不足和后来者可以努力的研究领域。在现有的外交场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女性的参与身影了,但对于外交领域中女性担任的职务高低、女性的决策权大小、女性参与程度的地区差异等等这些都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加以说明和评估,这些问题不免引人深思,给我们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启发。
注释
[1]Ethnographic approach:民族志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观察和/或与研究参与者互动。
[2]LGBT: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
[3]“Large-N”studies:“大N”研究强调从大量随机选择的案例中寻求模式。
[4] 刘爱华.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和现状[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05):23-27.
问题互动
问题1、如何理解外交机构中的“可预测”性别分工?
问题2、关于历史上女性对外交发挥的非正式影响,你能想到哪些突出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