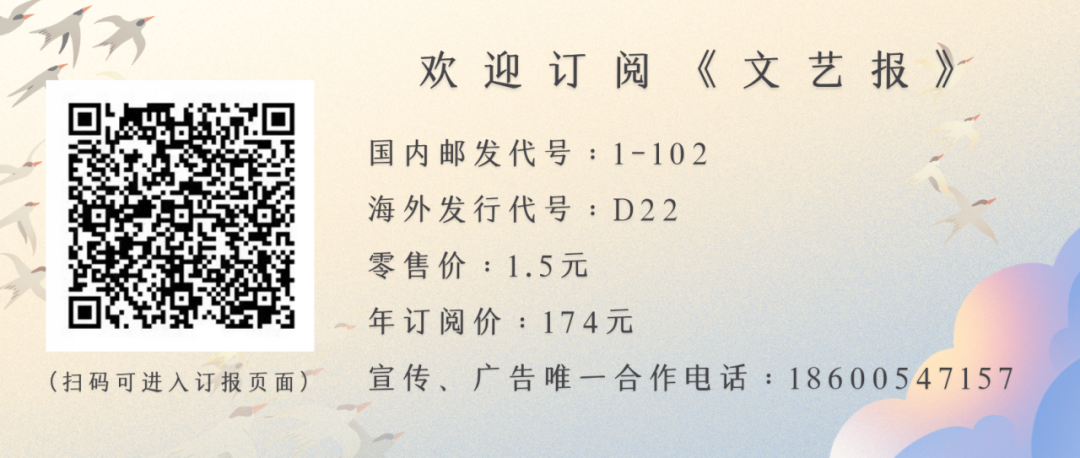批评家为明辨是非、激浊扬清,就必须以对话一方的身份,谋求与不同对象之间的深度交流。这些对象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与读者,也包括常见的创作定式和思想偏见。
文学批评要想发挥“引领风尚”的作用,完全可以借鉴中国文学的说书传统,让批评家以说书人角色进入对话场域,通过革新话语风格和借鉴新媒介传播方式,在复述作品情节的基础上追求批评的人民性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自《讲话》发表十年来,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深入学习和领会讲话精神,在反思批评的危机和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体系方面用力甚勤、贡献良多。单以影响而论,这段时期内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转向最是引人瞩目:评论界“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通过“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将朴学传统和实证精神引入文学研究,在以史代论、论从史出的方法论变革中,逐步克服了早年文学批评中常见的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现象。与此同时,为避免文学批评历史化转向所导致的对“文学性”研究的损害,评论界近年来又持续开展理论反思,力求在历史化批评中保持审美感觉,以期能让批评真正发挥“引导创作”的现实功用。
不过理论构想与批评实践之间总是存有差距。尽管评论界通过多年努力,已大大改善了文学批评的整体状况,但批评的危机却依然存在。一个典型症候是,批评家因缺少自觉的对话意识而习惯于自说自话,封闭私密的阅读感受既不能实现与作家读者的有效交流,同时也无法借此“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于是批评的独语就很难构建起以“对话”为标志的公共空间。问题的关键是,文学批评为什么一定要有对话意识?它对文学批评的思想方式和话语风格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文学批评要有对话意识
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学批评的论述中,“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虽然言简意赅,但它既是评论界改变批评困境的指导性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可以付诸实践的方法论武器。前者无需多言,批评若不能追求真理,仅仅止步于“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而追求真理的方法正是辩论,辩论即对话。更具体地说,批评家为明辨是非、激浊扬清,就必须以对话一方的身份,谋求与不同对象之间的深度交流。这些对象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与读者,也包括常见的创作定式和思想偏见。简言之,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最忌无的放矢。可是在当代批评史上,批评家要么执持于观念神话,以研究对象为依据去佐证某种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要么耽溺于历史崇拜,巨细无遗地搜罗外围史料以示博学。如此这般,很容易遮蔽文学作品这一批评对象。当然会有一些人认为文无定法,以作品为引子,批评家尽可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六经注我”式的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创作?不过主张打破批评与随笔文体界限的看法虽无不妥,有时甚至还会激活批评的生命力,但如果批评家不以分析作品为本位,不以提高创作为旨归,那么这样的文学批评就不具备现实功用。而文学批评一旦不能引导创作,则新时代文学理论的构建也将缺失重要一环。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具有对话意识的文学批评如何付诸实践?一般而言,批评家主要以作家为对话对象,他们从作家创作谈和作品内容中寻找话题,以虚拟对话的形式展开理论思辨、逻辑推演和审美鉴赏,尤其擅用文本意图比对作者意图,借此总结成败得失,引导创作实践。不过这种对话形式较为隐秘,通常是批评家主导辩论走向,比如他们会预设立场,以一己之见对作家创作谈和作品内容进行创造性阐释,由此展开的对话也就容易遮蔽作家的声音。有鉴于此,为保证对话双方的平等,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开始转向访谈式的对话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对话批评古已有之——从《论语》到苏格拉底对话,再到巴赫金和托多洛夫等人的对话美学,对话批评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虽说因受限于现代学术学科建制的形式规范,对话批评也曾一度式微,但近年来随着当代文学批评对话意识的回归,这一古老的批评方式又重新趋于兴盛。

孔子像
不过更进一步看,以上两种具有对话意识的文学批评仍有不少问题:首先是遮蔽作家声音的虚拟式对话徒有交流之名,却依旧克服不了批评家自说自话的毛病;其次是访谈式对话批评尽管在问答形式上保证了批评家与作家的身份平等,但总体上仍有一种“机锋不可触”的封闭感。明明是最需要理解批评家和作家对话深意的读者,却经常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样,始终徘徊于批评文本的迷宫之外而无法一窥堂奥。这说明访谈式对话批评有时也不能实现对话的敞开。问题就在于,如果访谈式对话仅仅是文人雅士之间的知音唱和,容纳不了广大读者进入对话语境的话,那么批评的人民性也将无从谈起。也许会有人说,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或在读者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相关经验匮乏,还有理解方式固化等等,都有可能使读者无法融入对话语境。但批评的要旨不就在于“敞开”一词吗?批评家解读作品,应该是为了向读者敞开其中的思想要义和美学旨趣。访谈作家,更是为了敞开他们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情境,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作品。这些事项,哪一样不是批评家的责任之所在?就此而言,批评家与其要求读者提升阅读与批评文本的能力,倒不如反思自己怎样才能做到批评的敞开。
说书传统与批评空间的敞开
其实只需深入观察,就可发现为何很多批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说自话问题。一个主要原因是,批评家尽管具备了对话意识,却总是要为对话场域设定准入门槛。他们通常以读者熟悉作品、同时又具备相关理论知识为前提,对话过程中无视读者参与,一味沉湎于和作家的精神交流。于是这样的批评文本就让那些没有读过作品,同时对作家经历与经验又不甚了了的读者如雾里看花般无所适从。更致命的是,很多批评家还有一种偏见,即认为自己是作品的评判者,价值判断要高于事实陈述,因此介绍作品故事情节、交代人物命运起伏等基础性工作就难入批评家法眼。从写作心理上说,跟着作家亦步亦趋地重述作品内容,又怎能和精深高妙的理论思辨相提并论?批评家这种潜在的傲慢,实际上已让文学批评沦为了少数人的精神生活。那么,究竟该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在我看来,文学批评要想发挥“引领风尚”的作用,完全可以借鉴中国文学的说书传统,让批评家以说书人角色进入对话场域,通过革新话语风格和借鉴新媒介传播方式,在复述作品情节的基础上追求批评的人民性价值。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有可能在敞开自身的同时另辟新途。为阐明这一观点,兹简要从说书传统谈起。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讲故事伎艺,说书兴起于宋元时期,在勾栏瓦舍间流传甚广、绵延不绝。说书人摇扇拍桌,一句“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不知可以唤醒多少国人的民族记忆。它是民间伦理的艺术载体,借助述史和演义,说书传统既反映历史亦传承文化。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于“‘模拟’或‘保持’的口头文学诸特征,以至文学史上一直用其形式特征称呼之:‘平话’,‘话本’,‘拟话本’或‘说部’”。有学者认为,“这么一种说书人的外衣,脱了几百年没脱下,到了清代吴敬梓、曹雪芹创作《儒林外史》《红楼梦》,应当说已是相当书面化的小说,可还是保留了说书人腔调及其相应的一批叙事技巧。”换言之,说书传统从宋元话本形成,经由文人拟话本和明清章回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直到清末民初受外来小说的冲击才逐渐消解。从1990年代开始,说书传统开始在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领域全面复兴,莫言、金宇澄、贾平凹、苏童、王安忆、叶兆言、格非、刘震云、叶舟、李修文等人都有意以说书人姿态创造性地发展传统文化与文学。时至今日,当代小说与说书传统已经变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这一现象不难理解,作家作为讲故事的人,写小说自然离不开说书技艺,但为什么文学批评也要重视这一传统?
如前所述,要想真正做到批评的敞开,批评家就应降低对话场域的准入门槛,他有责任向对话双方之外的读者交代话题背景。如果讨论的是一部文学作品,那么批评家理当复述故事、简介人物和概括主题。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普及作家创作——虽然通过批评向更多读者介绍作品本就是批评家的一项职责,但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为了敞开对话场域,让读者明白对话双方是基于何种论据展开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中的复述环节就成为了对话的前提。然而,如何复述又是一门艺术,高明的复述者从不照本宣科、按部就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定而后动:从原作哪里捡起叙述话头,如何瞻前顾后、左右逢源,又怎样千里伏脉、细节连缀。凡此种种,皆可反映复述艺术的本质就是以布局剪裁之法重写原作。其间自有误读乱谈之处,但如何复述、怎样重写,却能反映批评家作为读者的理解方式。
“讲故事”让作家批评受欢迎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近年来持续繁荣的作家批评,他们借由说书传统复述研究对象的方法,或可真正敞开批评的对话空间。

莫言、余华、苏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
有关作家批评的缘起、发展和特征,学界已多有讨论,其中作家驻校制度的推广最为关键。当作家化身为文学教师跨界批评之时,他们在课堂现场的批评实践便大体上还原了说书情境。与专任文学教师相比,驻校作家授课多以讲座形式进行,而讲座本质上就是一个现代说书场。主讲者立于台前,为吸引观众尽显神通:面对原作,他们或是制造悬念重述情节,或是攫取片段细读深究,抑或是讲到紧要处另起话头,以“闲中着色、无事生非”之法提振听众兴味……种种叙事的紧凑、中断或延宕,皆是说书技艺的临场发挥。在这样的文学课上,作家批评以复述经典作品故事情节的方式,取代了传统批评的理论阐释。这当然是作家在跨界批评时,仍然念兹在兹的一种说书本能。借由这样的复述艺术,作家批评庶几敞开了文学经典的文本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批评家代入说书人角色,那么他就会无时无刻不考虑听众的感受。虽然这一关怀在说书传统中主要是基于商业考量,但只要眼中有听众、心中有读者,那么批评就能真正地具备对话意识。再进一步看,批评家作为说书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为了照顾听众(读者),批评话语必须通俗易懂。由此,“话体批评”的复兴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话体批评”起于宋代,由诗话创体,继之以词话、小说话、文话等形式流传。其表现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等均或用之,其题名多缀以“话”“说”“谈”“记”等字,所谓“即目散评”者是也。由于“话”的意思就是“故事”,因此话体批评“体兼说部”,是说理与叙事杂糅的研究方法。而作家批评尤其擅长运用“话体批评”知人论世和谈艺说理,其文体形式有突出的“话性”(故事性)特征。这也是为什么较之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的受众面总是要更为广泛——毕竟听故事远比接受理论规训更让读者有参与感。对擅长讲故事的作家而言,文学课的“故事”往往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家以说书人身份演讲文学经典,复述名著本身的故事内容;其二是作家讲述个人的阅读史故事,交代在何种境况下与经典相遇,文学又如何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这种以阅读经典为起始,返诸自身又推己及人的方式,实足以感奋听众,尽显文学批评“熏浸刺提”的教育功能。而话体批评犹如说话聊天的句式、语气和腔调,既通俗易懂又饶有趣味,因此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学普及方式,作家批评显然有助于学院派批评进行自我反思和不断完善。两者之间的取长补短和兼容共生,或许是振兴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
“学术规范”和媒介变革的影响
不过提倡文学批评的对话意识和说书传统,还必须面对一个批评体式的变革问题。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以文章著述为载体,尤其是随着现代学术学科建制的完备,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即意味着撰写批评文章。受体例、篇幅和发表刊物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批评家要想在一篇文章内既复述原作又展开对话显然不太现实,甚至是漫谈闲聊的话体风格也会受到“学术规范”的排斥。在此状况下,文学批评其实大可不必拘囿于批评体式。批评家应该明白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远不是发表的成果数量和刊物级别,而是他的批评实践是否能够引发作家和读者的思考,能否真正引导创作。这就意味着繁荣文学批评还必须打破唯论文和唯著述的怪圈。批评家只有超拔于绩效优先的学术神话,重视批评体式的多样性,文学批评才能真正实现对话的敞开。目前来看,虽然学院派批评在这方面还有待进步,但作家批评备受欢迎的讲座和文学课形式,业已昭示了批评体式的变革前景。
与此同时,新媒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也越来越值得重视。近年来,文学视频的崛起十分引人瞩目。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方式,文学视频是依托网络平台,通过融媒介视频载体,以解说诗词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批评。它继承了宋代以来的说书传统和话体批评,在引领大众走进文学世界的同时,重新搭建起文学文本与普通观众之间的桥梁。整体来看,文学视频是文、图、影、音相结合的融媒介说书形式,媒介的多样性及其情景融合效果,不仅制造了更深的沉浸体验和更大的思想空间,而且也真正实现了对话的敞开。一个简短的文学视频,既有视频博主的情节解析和价值判断,也有观众不计其数的弹幕和评论。作为一种内嵌于视频之中流动的表达受众感受的文字,B站等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很接近中国文学的评点之法,它同时也是生成复调效果的个体声音,足以让文学视频呈现“众声喧哗”的效果。观众的深度参与,已经让文学视频成为了一种人人皆可在场的文学生活——批评也由此在走向大众的同时具备了人民性品格。尽管有学者担忧这种来自民间的批评话语形式,有可能会在大众趣味的更迭中失去可持续性和成长性,但新生事物对传统批评体式的强劲冲击,却一再证明了文学批评总有绝处逢生的蓬勃之力。
综上所述,如果评论界能够真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真理越辩越明”中体察批评的对话价值,那么就有可能在赓续说书传统和话体批评的批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文学批评引导创作的现实功用,继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相关阅读: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季水河:以新视野开拓文艺新境界
潘凯雄 | 文学·时代·时代精神——关于文学创作与表现时代精神的札记
白烨:新时代文学近十年来发展述要——万紫千红总是春
南帆:文学何以现代——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当代文学
王勇: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易伟平: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电视艺术创作的成就与启示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9月6日2版
微信编辑:王泓烨
二审:许婉霓
三审:李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