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生日已过,我已经整整五十四岁了。回顾过往,我惊奇地发现,“二十七”竟然是我在农村生活和到县城工作的分界岭。从咿呀学语到组建家庭,从少不更事到一名新闻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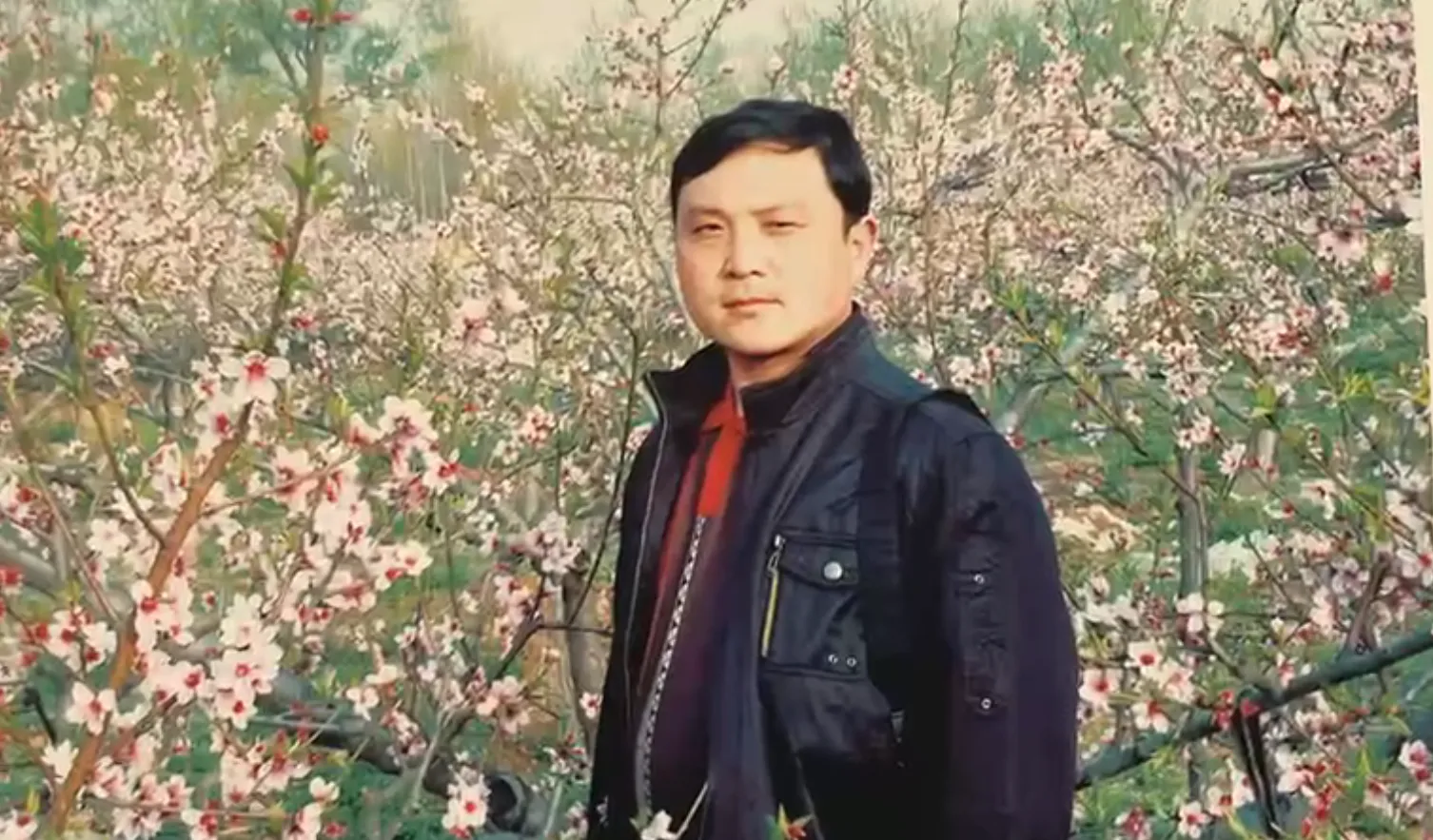
前二十七年,我经历了人民公社、大集体、改革开放。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弟兄姐们三四个,甚至更多。那时父辈们的生育观是,“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怀上了便生,生下来就养,尽管面临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贫困窘境。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吃饭穿衣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接受更好的教育便成了农村孩子更为迫切的需要。我们村在周边村里算是大村,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办过高中。尽管到我上学时高中部已经合并,但初中小学还在,学校的规模还不小,我的学业就是在我们村完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初中招考的中师中专生很是吃香,不仅上学有补助,毕业还安排工作,成为公家人、吃商品粮。从那时起,平日里亲如弟兄的玩伴们都明里暗里成了竞争对手,就看谁能通过考学跳出“农门”,为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族增光。但招录的名额实在太少,一个县每年考取的学生都很有限,更别说乡下一所普通的初中。我也很自然地与这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失之交臂,最后在我们镇上读了高中,之后便在外面四处闯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在学生时期懵懵懂懂爱上的文学,虽然没有让我的学业有所成,但这一爱好的积累和沉淀竟在打工中排上了用场。我在北京的几家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尽管是一些火柴盒、豆腐块,内心里逐渐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从北京回来,参加县里的招工考试,被教育部门录用,在村里一所初中代课,闲暇之余写一些长辈们抵触、同事们不解的文章。心里一直有个梦,梦里面全是文学和新闻。
梦做久了真的会成真。1996年春,洛阳日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在家人的支持下我自费到报社学习,文学素养和新闻写作能力迅速提升,不断有小短文在《洛阳日报》上刊发。我在《洛阳日报》上发表文字的消息引起了当地镇党委的重视,把我从教育上借调到镇里专职搞通讯报道。短短八个月时间,我便在《洛阳日报》上发表了几十篇新闻稿件,有一篇还上了《洛阳日报星期天刊》的头版头条。第二年一开春,县委新闻中心竟把我从镇里“挖”到县里工作。

从1997年4月到县委新闻中心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里,从一般新闻干事到新闻管理,当过报社的通讯员、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干过新闻中心的副主任、主任。随着县级媒体的融合,还干过一段时间的融媒体总编辑。后来曾调到县党史研究室工作,本以为这次便要脱离新闻宣传岗位了,不料四个月后,我又被组织安排到网信部门工作,从监督的层面从事着新闻宣传工作。

从报社的通讯员,到融媒体的总编辑,再到网信部门,我算是把传统媒体、新媒体所有的行业干了个遍。二十七年下来,纵向来看,发表了不少作品,印了几本作品集子,但横向与周边的同行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值得庆幸是还没有把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丢掉,仍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县里的正能量宣传采访、写稿,为树立对伊川外形象“鼓与呼”。

二十七年前初到县里工作时,孩子还没有出生,如今孩子都参加工作几年了,在一家单位负责着平台信息的编辑和维护,每当看到孩子单位的公众号上出现她的名字的时候,我总从心底升腾起一种自豪感——事业后继有人、家庭后继有人,我感到充实而满足。
五十四岁,两个二十七年,一大半的人生献给了新闻宣传事业。今年的“中国记者节”当天,单位的好几个同事还郑重其事的祝我“节日快乐”,弄得我一脸愣怔。想想很是惭愧,写稿三十三年,专职干新闻宣传二十多年,竟然连一个记者证都没有混上,却也跟正规媒体的记者一样过了二十五个“中国记者节”。

生日前夕,我在思考,自以为还能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再干它几年,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新人换旧人,如果有朝一日不在岗位上了,吃饭的本领不能丢,在这如钢铁洪流般的事业中,再干上二十七年,抒写新时代,也抒写自己文学和新闻的春天。
(葛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