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冯杰在散文创作中有意建构一种文学地理学,在《鲤鱼拐弯儿》《非尔雅》等作品中创造出一道独特的北中原景观。冯杰在《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一书的自序中就写道“私家文学地理符号称‘北中原’”。现实生活中,冯杰主要生活在豫北地区。冯杰没有将地理学名词直接在自己的作品中套用,而是将“豫北”命名为“北中原”,体现出他对两者不同的思考。后者作为现实中地理称谓的变体,并非现实地点,而是作者着意建构的一种文学景观。
在《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一书中,冯杰则将自己书写的地点转移至了开封,试图构建出一道名为东京的景观。与之前作品不同,本书有更多的历史书写。但作者并不追求对宋代东京的真实还原,而是在作品中让现实中的开封与历史上的东京进行互动。这种互动打破了古代与现代的界限,也打破了作者与开封之间的界限,使这一地域具有鲜明的“冯杰风格”。
那么,作为文学景观的东京,与它所再现的真实地点之间有哪些不同?这种从地点到景观的建构中,历史与现实,主体空间与他性空间,诗性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文学书写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即试图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自我中心视角与诗性景观的生成
与传统地理学或者常规地理学的“地理中心”不同,冯杰在《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中,坚持了一种“自我中心”的视角。在文学地理学家理查德看来,现实地点相比,景观具有更多的主体性特征。《闲逛荡》一书中的景观,就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在具体行文中,作者主体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作用力,对象和他者都围绕着这种主体经验而旋转,如苏东坡不是历史上的苏东坡,而可以为这本书写序。冯杰还在跋中交待如何让苏东坡写序,写明饮酒以及做梦,是让苏东坡作序的必要条件。而在跋中苏东坡也再次回函,并且写到了“房贷首付”等现代经济学词汇。这种古今穿越式的对话,让本书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性特征。
书中写到的景观,还有着更多心理和情绪的投射。在这种自我中心视角和强烈主观性书写中,历史真实并不成为一种限制,反而要契合文本氛围的要求。如到明时文人才开始学习抽烟,但它可以出现在《闲逛荡》的文本之中。作者并非没有常规的历史意识,而是说:“宋人为何不能提前抽上两口?”。
这种自我中心视角映射的主观性,制造出了诸多诗性话语。如在书写香料胡椒传入中国的路线图时,作者以一种诗性话语来呈现:“胡椒在暗处行走。”这样的诗性话语在本书中异常丰富。在写到诗人徐玉诺时,作者写他的诗集“像一座荒芜的花园。”作者的描述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诗的态度,本身即饱含诗意。
这种诗性话语不仅仅出现于本书抒情的篇章或段落中,也出现于叙事性文字中。在《寓言:骆驼鼻子法则第二则》中,作者也以诗性话语来结构叙事。如寓言最后,“主人死了,连两只真皮靴子也都在外冻死。”
这样的诗性话语也出现在本书刻意建构的主线故事中。如对头发像荒草的人的书写:“他头碰撞着名词,腿敲着动词,目灌注着形容词。”这样的诗性话语,营造了叙事的诗性氛围。
这种诗性书写一直延伸到对地方性知识中诗性思维的发掘和呈现。作者在本书中写到了诸多蕴含着神话思维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神话思维,就是一种特殊的诗性思维。如书中写到的马都有夜眼,这夜眼除了走夜路,还可以避妖驱邪。作者还为之附录相关的拾遗与图画。夜眼在这里又不仅仅是地方性知识,同时,也因为在众多中国古典画作中的出现,成为一种艺术知识。这种知识考古式的书写,揭示了精英文化中诗性思维或者说神话思维的影子。
在这样一种知识考古以及诗性探索中,雅与俗的边界也是可以打破的。雅俗边界的打破,正是宋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宋词在这一时期文学的正统地位,就是经历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柳永作为一个科举不得志的底层文人,成为一代词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宋代文化的市井化所呈现出的一种民间取向,与作者在文章中所呈现的民间气质并不矛盾。作者的这种写作策略,和北宋的文化氛围之间并无特别大的差别,也使之显得并不特别突兀。
作者在食篇的书写中,也将饮食写得重过于风雅之事。如“桂花铺得再厚,终究压不住他文字里迸溅的唱菜声,在那香气里断断续续。”唱菜声,能够穿越桂花,就是饮食大过于那些风雅之事。唱菜声所唱出来的也不是那种可称为雅的美食,而是“扒羊肚……爆腰片儿……”等更为市井化的菜肴。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并不厚此薄彼,显露出一种文化态度。
这种对雅俗古今对立的跨跃,也如韦斯特法尔所言的跨界:“跨跃边界在此指从一种心态跨入另一种心态,从一种精神跨入另一种精神,始终保持动态,与停滞、静止相反”。
冯杰在《闲逛荡》中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跨界心态。本书“闲逛荡”的精神正如本雅明的游荡者一样是一种跨界。跨界者典型的特征就是对身份本质主义思维的丢弃。冯杰就是以一种“去身份化”的视角来书写开封的,因为开封并不是他成长的地方。在本书写作中,他将自己北中原人的身份一定程度上忘掉,进入到开封/东京的场域之中,体验、想象并书写这里的一切。
这种自我中心视角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主体性,而是诞生于其身份的杂多性之上的。这样一种多元混杂,将雅与俗,民间与精英融为一炉的主体性,是一种饱含现代性的主体性。在这样的主体视域下,本书的结构也是一种循环往复,书写语言,也成为一种循环往复。作为诗人的冯杰,明白语言其实永远处在一种循环往复之中。这种书写,体现了他本人,对于空间、地方和语言的深入的理解。

主体间性书写与杂语中建构的地方
在人本主义地理学中,地方成为与空间相对的词语,是价值和意义积淀的空间。而地方的意义,是一种主体间性创造的结果。对地方的再现与表现,最恰当的方式是采用多重聚焦的视角,以多种视角的交叠与互动来完成。这样的书写才能够矫正不同人群的文化视差,呈现出地方的多元性特征。冯杰的《闲逛荡》,就是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乡村的、城市的等等多种视角的交叠和互动,而开封在这本书里,也是一种多元的,混杂的开封。
这种主体间性的书写,首先体现在作者对感官空间的塑造上。承载衣食住行和玩乐的空间其实都可以列入感官空间。而最能体现人类空间的感官性的,就是特定空间内的美食。开封是一座美食城市,冯杰对美食的书写,也几乎贯穿了整本书。韦斯特法尔认为:“人类空间是一个感官空间,其细微之处都应该由集体定义(特别是文学集体)。”对开封美食的发掘和的撰写,其实就是发掘由数量最多的市民集体定义的感官空间的微妙之处。
这种多元融合的地理经验中,作者还加入了诸多不同阶层的观察视角,甚至包括乞讨者:“大概是我姥爷当年串巷要饭谋生得到的地理生活经验。相当于口头东京指南。”胡同相当一个城市的毛细血管,要饭者对它的理解,是与常人不同的。乞讨者的地理经验,也让开封的地理经验更丰富。而叙事者姥爷的这种边缘和底层身份,也促成了冯杰对于边缘身份更多的认同。
冯杰的《闲逛荡》,一方面是精英视角,通过与苏轼、黄庭坚、孟元老这样的文化精英进行对话与思考;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一种底层边缘视角。尤其在呈现正统或国家话语时,他所选择的是一种边缘化的民间视角。如对吆喝的书写:“宋徽宗和武大郎都喜欢吆喝。”用“吆喝”这样一个词概括阅军的唱诺和叫卖炊饼之声,就是在用民间视角来解读国家话语,让两者具有等同的地位。这也是作者的一种书写策略:他试图在书写中对边缘进行赋权,即让边缘有更多的话语权。将开封方言进行正式化和历史化的呈现,其实就是让作为方言的语言,加入到更加正式化的语言与权力表达中来。所以冯杰为方言进行举例,并不是纯粹的调侃或者搞笑。
《新东京方言汇考》不仅提供了方言的解释,还要进行造句。如宋徽宗让官员们进谏时发言“朗利”些。这些造句使方言融入到一些独特的场合中,与其说是增进了人们对方言的理解,不如说是这些方言增进了文本的杂语性、反讽性和趣味性。这是与诗性话语不同的语言。
虽然《闲逛荡》中有诸多的诗性话语,冯杰却不只是一个诗人。诗人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消除了他人的意向与语调,形成了语言的统一性与封闭性,一般不存在杂语性和对话性。在冯杰的这本书中,冯杰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但却不仅仅止于此。他还承认自己身份的杂多性,更注重对社会多个阶层话语和古代话语的吸纳与呈现。如书中写到卖豌豆糕者的话语:“要不是我家祖上的豌豆糕,他能画出《清明上河图》吗?早都饿死个屌朝上了。”在《细节的毛孔正在张开》一文中,作者更是以“卖葱者语”“卖西瓜者道”“卖饭者说”“卖甘蔗者言”等等来结构全篇,还对小商贩的话语进行了细分。
在对多种职业、阶层与体裁进行模仿之后,会有本书叙述人的话语呈现。这一叙述人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构性,与作者冯杰本人并不完全等同;这其中还要穿插直接的作者语言。作者语言的介入,呈现了一种现代性知识与历史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如作者对东京衣着的考古中,涉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但更多的是对于知识的考察、追问和探究。这样的探究和探讨,使用更多的是现代性知识。如在《裁缝小传》一篇的补记中,作者用阿德勒的话语“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来对母亲裁衣进行总结,就是一种现代性知识。因为古代并没有儿童心理学甚至明确的儿童概念。这样的现代性知识、现代生活经验与历史知识产生了深入的对话,成为了对历史知识的一种激活。历史活在《闲逛荡》一书中,并不是如历史本来面目一样,而是像苏东坡给本书写序一样地活,是活在作者的文学想象中。
作者的介入,也使他用现代语言对历史事件进行重述。这种重述,构成了一种语言修辞上的陌生化,也构成一种讽刺性模仿。如作者对智取生辰纲一事进行描述时,将晁盖等七人称为“七人行动小组”;如将宋徽宗的“嘉言懿行”四字说成是对李嘉诚话语的褒扬。这种解释其实是对当代话语的讽刺性模仿。其讽刺的锋芒也指向了当代。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的交织与互动,构成了另一种杂语。
巴赫金认为“在每一具体时刻,都有社会和思想生活中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语言并存。”因此,《闲逛荡》中杂语的书写,不仅有各个阶层的杂语,这是一个城市的共时性存在;同时还有不同时代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城市历时性的存在。
这些语言和视角的主体间性呈现,增加了地方性知识的丰富性。地方,并不只是属于某种圈子,某个阶层,甚至某个时代,而是多种阶层和时代的共在。冯杰为这种共在,找寻并创造了一种共在的语境,也营造出了一种丰富的地方。

虚构性叙事与他性空间的联接
《闲逛荡》是一部文体界限模糊的作品,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用散文来书写一座城市,而是加入了虚构性叙事。因为冯杰对开封的书写,并不执著于对历史和现实开封的真实还原,而是想要创造出开封的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虚构性叙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虚构性叙事的加入也与作者对开封的定位也有关系。作者在序言中,就将开封定义为“情城”,叙事的加入,也是在为之增加情感的丰富性。因为情感是流动的。在当代情动理论中,“没有一种情感是固定的,这是就是情感的变化。”而要书写情感的变化,则要进行叙事。用相对静态的描写等散文手法,不足以表达这种情动变化的。能够被称为情城,肯定要成为情感的发生地,而情感中最浓烈的爱情也就成为必要的书写对象。作者就在衣食住行的章节中,插入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爱情的叙事线。如在《东京水果类别》一节中,作者以一句与整文毫不相干的话语:“在相国寺拐弯处,忽然见到你。”“你”的出现,证明叙述者的叙述是有对象的。在这一篇章中,并未交待“你”是谁,而是留了一个悬念。《在东京向火》一文中,你又出现:“你穿着一袭墨衣……映照你洁白的面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叙述人的言说对象是一位女性。作者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让这一线索,如冰山一角般浮现。
这种叙事也并不是一种线性时间叙事,而是按照一种空间化的叙事方式,将其分割,散放在多个篇章的角落。书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即头发像荒草般的男子,作者对他的叙述也是如此。
这种叙述方式,与本书对于历史的叙事策略相同,是将时间空间化的写法。冯杰并未完全按照历史书写的方法来写一部城市史,而是按照衣食住行等把那些历史分割开来讲述。而在不同的篇章里,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不仅镶嵌在行文中,也镶嵌在当代生活中。在当代日常生活中镶嵌的,不仅有历史,还有记忆,而不管是历史还是记忆,都是依托具体空间来呈现的。在本书中,同一空间可以容纳多重的时间,成为书写历史的方式,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连续性。
贝尔唐·韦斯特法尔认为:“如果用线来象征空间的连续性,那么这条线就该是逃逸线。人类空间既面对时间又在时间之中,它是一座花园,里面布满了通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的小径。”
《闲逛荡》就是对开封/东京这一空间的逃逸线式呈现。有诸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向了这座城市。作者这样的书写,使开封并不是封闭僵化的一体,而是像一种相互联接的群岛。群岛诗学在《闲逛荡》一书中有着深刻的呈现。作者不仅写了开封,更书写了作为开封他性空间存在的城市。这与文学地理学对空间再现的认知是一致的。在文学中,“世界存在于它与生俱来的他性中,也因这种他性而存在。”
正是通过虚构性叙事,作者使开封在时空层面,完全向他性空间敞开。而这种他性空间的建构中,两个虚构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东京,又与现实开封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是带有明确虚构痕迹的头发如野草般的男子。他原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不仅出现在叙述者梦中,还出现在第三届“《清明上河图》国际研讨会”上。正是他建构起了从开封进入历史上“东京”的一条垂直线,成为开封他性空间建构的重要线索。
开封他性空间的建构,不仅是垂直线上的,而且有水平线上的,那就是日本东京。本书写到的白橙就是连接起开封他性空间的另一个人,是冰山渐露真容的那个“她”,也是本书叙述的对象。书中白橙最后离开开封,所去的地方是东京,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虚构,让这两个名称有联系的地方,在这个文本中建立起强联系。这种文本中的强联系,也是对空间流动性的证明。而全球化正是它的一个背景。这两个人物也成为两条进入开封/东京的线索。垂直线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东京,而水平线则是日本的东京。垂直线和水平线的书写,建构出了两条进入东京的线索,也建构出了开封的他性存在。这种他性空间的书写,进一步延伸了本书的空间叙事线索。通过这种逃逸线式的叙事,对开封的书写,脱离了种种身份的限定。贝尔唐·韦斯特法尔认为:“给城市限定身份的尝试往往是徒劳的,城市会从中逃离。”
这种身份限定的解除与脱离也体现在作者、叙事者与文学空间的关系上。在《闲逛荡》中,冯杰与叙述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冯杰为叙述者创造了自己的身份:他长居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者,又是一位诗人,宋学学会的成员。而冯杰则是一位“北中原人”,长期在新乡生活。这种地缘身份的转换,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转换与互动,呈现了一种不确定性。在书中,叙述人与作者身份不断重合,又不断产生间离和差异。在这种身份的转换过程中,东京的身份也在不断变换。
在将那些固定身份进行解构之后,开封所凝结而成的,不是那些外在的身份,而是作者所谓的记忆之城与情城。这是对地方核心价值的把握。正是这样逃逸线式的叙事,使东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空间与地方得以呈现。
德勒兹和伽塔利把领地看作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要经历不断的解域与再域化过程,而再域是为了下一次的解域。冯杰曾将北中原作为自己的领地,以方言和方言阐释写出了《鲤鱼拐弯儿》《非尔雅》这样的作品。在《闲逛荡》一书中,冯杰又再一次将开封再域化,而同时,他的书写也是一种解域化,将一般的旅行者内心对于东京的理解给解域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冯杰建构出了自己的私家文学地理,也建构出一种独特的地理诗学。冯杰以自我中心视角和主体性的张扬来完成对诗性话语的生产和诗性景观的塑造,以主体间性的书写来建构一种复数的地方,以丰富的杂语呈现地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通过虚构性叙事来建立与开封他性空间的联接,以独特的空间叙事方法来建构起一条空间的逃逸线,完成了对固有地方观念的解构,最终建立起一种名为东京的文学地理景观与独特的地理诗学。
原文刊登于《南腔北调》杂志2024年第8期,题为《地理诗学的建构与地方景观的生成》
作者简介
张艳庭,文学博士,任教于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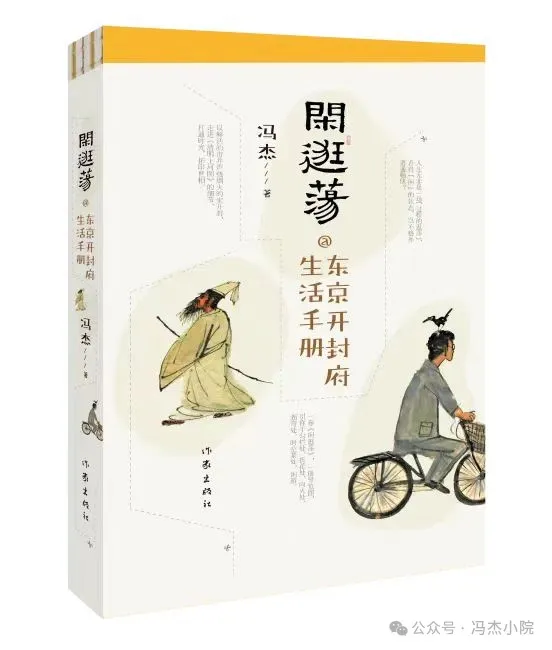
冯杰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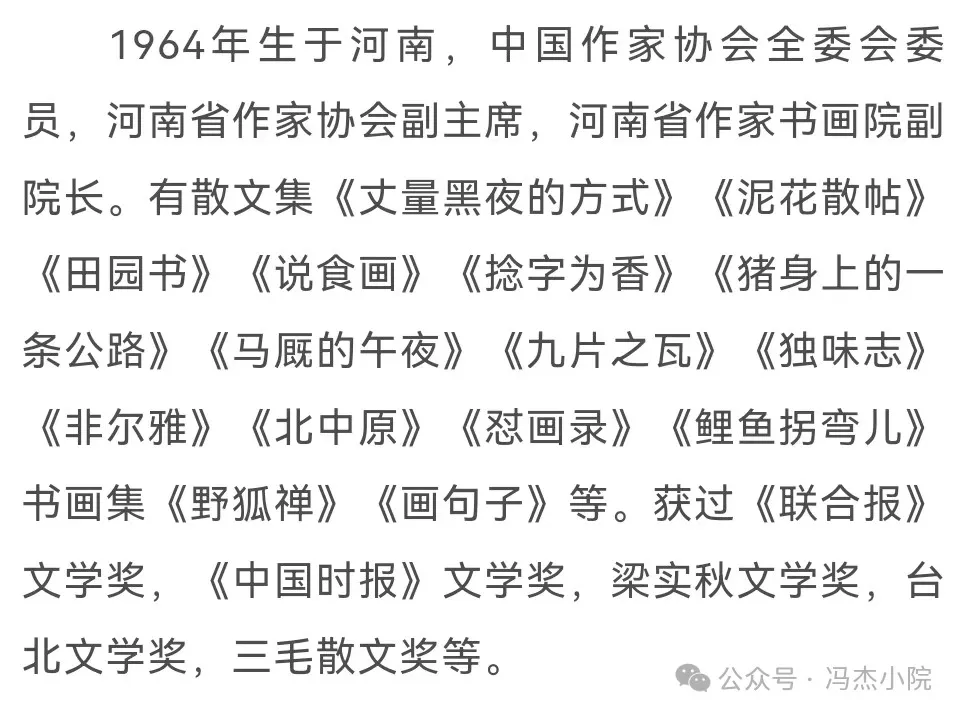
来源:冯杰小院
